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潮頭看歷史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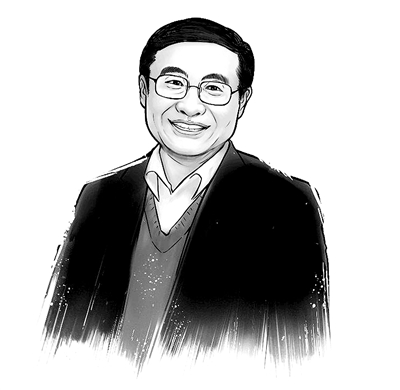
李捷,祖籍山東平陰,1955年2月生於北京。1969年12月參加工作,1973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求是雜志社社長、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毛澤東生平和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著有《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歷史貢獻》、《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等,編著《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多部中共文獻資料,《毛澤東傳》的主要撰寫者之一,《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歷史理論經典著作導讀》首席專家。
“論從史出”,這一直是中國傳統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優良作風,發揚至今
記者:李會長好!您長期從事毛澤東研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請您結合自己的研究經歷和這兩部國史著作的編撰經驗,談談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精神。
李捷:我認為最基本的,也是一以貫之的,就是實事求是、秉筆直書,這是最可貴的中華史學精神。搞史學,首先要把歷史事實弄清楚,要掌握第一手的歷史資料,由此建立認識歷史的基本框架,進而形成我們的判斷。我們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論從史出”,而不是帶著主觀的結論去尋求各種材料——這是最基本的精神,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尊重史實、實事求是,這是史學工作者最基本的良知,也是職業道德。從這一點來說,這是史學的命脈。
記者:實事求是,論從史出,可以說也是中國史學的一個主要傳統。
李捷: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也是如此,首先強調一定要從材料入手。馬克思當年研究五種社會形態,作了大量的歷史筆記,在研究歐洲歷史的同時,還研究了亞洲生產方式、東方文明的歷史。他對摩爾根關於史前社會歷史的研究也作了詳細的摘抄、認真的研究。在查閱大量資料的基礎上,他才總結出五種社會形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馬克思才能從唯物史觀和辯証唯物論的哲學高度來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他把人類歷史看成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漸演變的一個形態,既指出了人類的史前史是什麼狀態,又指出了人類歷史是怎樣經過一個漫長的有階級的社會,最后達到世界大同,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剝削,消滅了人壓迫人的制度,最后走向共產主義。這就是我們說的要有“史識”。更為可貴的是,馬克思第一次在史學研究中提出“世界歷史”的大概念,即所有的歷史不只是國別史,而是整個人類共同發展的歷史。它雖然是多樣化的,但是大致是循著一個共同的歷史規律來發展的。人類的歷史,不僅要看成是國別史、民族史,更重要的是要看成統一的世界史。這就極大地開拓了人的眼界。歷史資料和歷史理論,這兩者對於史學工作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得出的結論,既離不開最基本的事實,也離不開科學的理論指導。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做到“論從史出”,而不是先有結論,再去找材料,這是基本的要求。實事求是是史學的命脈,如果研究歷史的人不說真話,絕對經不起后人的推敲。
“論從史出”,這一直是中國傳統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優良作風,發揚至今。正是圍繞著這一點,我們的很多學科和研究方法,比如傳統的考據學、音韻學、金石學等才能運用到史學研究中來,而像考古學、人類學等等的現代學科,更是拓寬了我們發掘比對歷史資料的渠道。現在的歷史研究,不僅要處理見諸文字的檔案資料,還有很多鮮活的東西需要我們去考察分析。
記者:隨著信息時代和全球化的到來,歷史學家需要面對的檔案材料越來越多,同時研究歷史的方法和途徑也五花八門,越來越復雜。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歷史學家還原歷史真實的難度是不是同時也越來越大?面對紛繁復雜的檔案材料,如何才能避免盲人摸象?
李捷:歷史學者在梳理各種檔案的時候,會發現越靠近我們的歷史,資料會越多。怎樣通過這些材料還原歷史,認清哪些是代表本質的現象,哪些是枝節的東西﹔哪些是主流的東西,哪些是非主流的東西?一定要用科學方法來整理這些歷史資料,才能還原真實的歷史。你比如,現在一些所謂的“歷史揭秘”,就是經不住考証的,它其實就是“盲人摸象”。你拿來一段蔣介石的日記,說這就是真實的蔣介石,是沒有說服力的。具體到抗戰時期,大量的材料証明,蔣介石是有兩面性的,既有面對民族危亡時愛國的一面﹔也有其階級本性決定的反共的消極一面。這就導致抗戰后期,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一面越來越暴露出來。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后三年多時間就把大陸失掉了,被趕到台灣。這都是有歷史必然性的。所以說,如果僅拿蔣介石的隻言片語或者蔣介石日記某方面的說法,去否認他有頑固反共這一面的話,是站不住腳的。
一個合格的歷史工作者,必須在歷史的長河裡,把人類、社會、國家、民族發展進步的因素放進去,作為評價歷史事實的一個價值尺度
記者:上世紀80年代至今,國內引進了不少外國學者研究毛澤東的著作,比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的R·特裡爾的《毛澤東傳》,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的菲利普·肖特的《毛澤東傳》,曾經影響力都很大。我讀這些書有一個體會,就是面對同樣的檔案材料,中外的學者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如何看待這種情況?
李捷: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二個傳統。歷史是客觀的,但是面對同樣的歷史材料,史學家如何解讀,卻是主觀的。史學家自然地會受到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影響和局限。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史學工作者自覺地接受科學的理論指導。這個科學的理論,就是馬克思所奠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所以,同樣的材料,我們作這樣的解讀,西方的學者作那樣的解讀。R·特裡爾和菲利普·肖特等,他們的史學觀點就是用權力斗爭說來解讀歷史。如果權力斗爭學說是從政治結構來看問題的話,恰恰到了最后,它偏離了這個主旨,將歷史變成了私人之間的恩怨沖突。
記者:除了參與《毛澤東傳》的編撰工作之外,您還親自撰寫了大量的研究毛澤東的專著和論文。您提出了一個評價毛澤東歷史地位的“五大坐標”,包括馬克思主義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展、中華文明發展及世界文明發展等五個參照系。在這“五大坐標”每個都有“發展”兩字,這是不是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核心史觀?
李捷:唯物史觀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把一個人的思想和他對歷史的貢獻,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看他的哪些思想是前人所沒有的,而這些思想又是推動還是阻止了歷史的前進,把動機和效果結合起來。從20世紀至今,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歷史性巨變,就是由毛澤東開啟的。中國人終於可以在世界上站立起來,結束受盡西方列強屈辱的歷史,也是從毛澤東開始實現的。對於這樣一位對國家、民族、人民做出巨大歷史性貢獻的民族英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現在和將來都會永遠銘記在心。但毛澤東同志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鄧小平同志繼承了他的正確的一面,同時克服了他的歷史局限性,帶領我們走進了一個新時代,歷史就產生了從思想到實踐的飛躍。從人物與人物的歷史傳承關系來說,就產生了一次超越。我們整個的社會發展,就是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記者:從發展的角度來研究歷史,這與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有相通之處。
李捷:中國的史學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史學,都強調歷史的教育作用、借鑒的功能。一部歷史,就是進行歷史觀教育的好教材。一個合格的歷史工作者,必須在歷史的長河裡,把人類、社會、國家、民族發展進步的因素放進去,作為評價歷史事實的一個價值尺度。
歷史是客觀的,但對歷史的評價要體現正確積極的價值觀。不體現價值觀,所謂的歷史的純粹客觀中立是沒有的。在西方學者的筆下,同樣講拿破侖,可以有很多種寫法,有人把他寫成推動歐洲政治版圖的英雄,也有人把他寫成惡魔。寫毛澤東也是如此,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人的寫法。除了史學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不同以外,很重要的還有一點,就是價值觀。司馬遷寫《史記》,除了開創了中國史學傳統的貢獻,還有通過歷史來告誡后來的人們應當愛什麼、恨什麼。這種愛憎分明的史學傳統,也是《史記》不但能夠成為偉大的史學名著,同時也是不朽的文學名著的重要原因。
記者:那麼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用發展的觀點看歷史?
李捷:對於今天來說,我們應該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就像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歷史上不能沒有英雄,民族也不能沒有英雄,我們必須維護這些英雄。
現在出現一種匪夷所思的現象就是調侃英雄,很讓人寒心,很耐人尋味。說明一些人心裡面沒有道德尺度,或者是沒有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最高利益的價值尺度。若沒有這個尺度,就成了胡適先生所說的“歷史就變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說它好,它就好﹔說它是惡魔,它就是惡魔。不應該是這樣,歷史是有價值判斷的。岳飛毫無疑問是我們的民族英雄,盡管他所生活的年代是民族融合時期,但在當時體現的精神恰恰是中華民族寧折不彎的英雄氣概。在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系列活動中,我們既肯定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時也不忘記為民族大義犧牲的每一位烈士。這就堅持了中國共產黨評價歷史是非的立場,同時也堅持了中華民族的立場,把這兩個立場很好地結合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