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抗戰:“九一八”后中國知識界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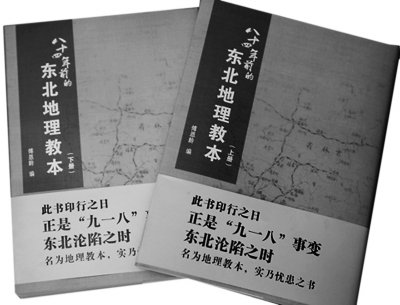
“全國同胞對此國難,人人應視為與己身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斗”
1931年9月18日,沈陽一聲槍響,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白山黑水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艱苦斗爭。遠在北平的知識界則以筆為武器,喚起民眾“以決死的精神”來團結苦斗。在北平各界著名人士的聚會上,傅斯年提出了“書生何以報國?”的話題,號召知識分子們反躬自問,探索救國之良方。
4天后,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就以學術報告的形式回應了傅氏的呼吁。22日晚,蔣在清華禮堂,主講《日本此次出兵之經過及背景》,在梳理日本侵華之來龍去脈后,指出若想解決東北問題,治標之法在於“(1)喚起國際同情,無大效果﹔(2)宣戰必敗﹔(3)排貨運動,惟一辦法”。至於治本之法,蔣氏認定“在於民族與個人之根本改革。中國人遇小事則萎靡不振,遇公事則貪婪腐敗,此種習性非大行改革不可”。
蔣氏此番演講果然激起眾多學子對東北問題之關注。不過要想喚起廣大國人對時局的重視,則需要報紙媒體的不斷宣傳。9月26日,著名報人鄒韜奮就在《生活》周刊上著文向全國民眾呼吁“全國同胞對此國難,人人應視為與己身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斗”,“如政府甘心亡國,我們不能坐視偕亡,當起而自救”。一個月后,左舜生也刊發《注意日本的所謂條件》一文,徑直指出:“日本一次的出兵佔領遼吉,完全是對中國抱著一個算總賬的態度,日本既下了一百二十分的決心,在他們是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勢。”既然國民政府不爭氣,那麼作為中國人,則必須力持與日寇死磕到底的態度,“假如我們也不抱定一百二十分的決心,也不抱定一個與日本算一回總賬的堅決態度,則不僅遼吉兩省有名存實亡之憂,就想要在最近的中日交涉上稍稍有一點補救,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
“東北問題之解決,在於吾人者多,而在於他人者寡。中國建設成功之日,恐即東北問題完全解決之時也”
國難之際,滿腔熱忱固然重要,尚需冷靜地思考與籌謀。若想全面深入掌握東北問題,則非有研究論著不可。就在事變發生四個月后,蔣廷黻原在南開的老同事傅恩齡,應校長張伯苓之命,編撰成長達數十萬字的《東北地理教本》,作為教材供南開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讀。名為地理教本,但書中內容已涉及歷史人文、地理風俗、行政交通、資源礦產、工業商業、租借地、中東鐵路公司、南滿鐵路公司及周邊經濟形勢、地緣政治局勢等諸多方面,資料豐贍,條目明晰,對當時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情形的介紹非常全面。正基於對資料、數據、輿情的充分搜集與佔有,故教本中所得出的觀點令人信服。如結論部分,編者提出了解決東北問題的消極與積極兩套方案,戰略眼光可謂長遠,同時著手之處又非常務實,可見其考慮之周全。文末編者更是強調:“東北之權益,既由吾人失之,故東北所失權益之規復,其責任亦應由吾人負之。簡言之,東北問題之解決,在於吾人者多,而在於他人者寡。中國建設成功之日,恐即東北問題完全解決之時也。”這一段文字,可謂點出了東北問題症結之所在。
此書能如此迅速地問世,與南開學人們平時的持續關注與學術積累及編纂時的辛勤與勞苦自然分不開。已故著名史學家何炳棣曾就讀於南開中學,他回憶道,彼時南開校長張伯苓注意到日本對東北地區的野心,“所以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早已囑咐校長秘書、精通日文的傅錫永(恩齡)先生,從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累年大量的調查統計資料中,選撮精要編出一本專書,以為南開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讀的教科書,定名為《東北經濟地理》。”張伯苓在1927年特意組建了“滿蒙研究會”這樣一個專門研究機構。此后南開大學不斷派遣本校教授赴東北考察,積累第一手的觀感與資料。這些教授,大多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的專家,如蔣廷黻主攻外交史與國際關系,諳熟近代以來中俄、中日問題。通過實地走訪,蔣認為“東北的政治措施,乃至全國的政治措施都是不夠的。軍政兩界的愛國分子都認為兵工廠、鐵路、出超的貿易是強國的條件。但是,他們忽略了健康、受過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強國的基本條件”。再比如擅長中國工農業經濟問題的何廉,一度致力於研究河南、山東百姓向東北遷移現象,他“越來越感覺到研究構成中國鄉村社會的經濟與政治機構,是極為重要的”。於是他借助赴東北考察的機會,搜集了大量寶貴的一手資料,用於該課題的研究。與此同時,正是由於編寫教本的契機,不少學者將東北問題作為畢生關注的重點。如蔣廷黻於1929年離開南開后,依然在該領域努力耕耘,發表了長達數萬字的《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一文,於學界引起極大反響。
除卻教材,學者們還紛紛撰寫學術著作,以証明自古以來東北就是中國的疆土,駁斥日本之歪理邪說。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不到一個月,“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擇此職業,無以報國”的傅斯年,便召集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四位頂尖歷史學者,聯手撰寫《東北史綱》。在卷首語中,他們道盡寫作的兩大初衷:“然而前途之斗爭無限,知識之需要實殷,持東北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於國事者焉。吾等明知東北史事所關系於現局者遠不逮經濟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僅有興會於史學之人,亦但求盡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諸?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一動機也”。再者,“就此二三千年之歷史看,東北之為中國,與江蘇或福建之為中國又無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用不著辨者,此吾等寫此編之第二動機也”。此外,供職於《大公報》的王芸生在事變后不及兩年的時間裡,寫出了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成為當時研究中日關系史必不可少的參考書,甚至引來日本史學界的異常關注。可見基於學術專長,以期有裨於國難,是讀書人大多依循的路徑。
“鞭策政府,以度此空前非常之國難,此真愛國志士所當劍及履及求其實現者也”
當然,作為有良知的學者,內心總免不了有些“忍不住的關懷”,於是手中之筆便飛出書齋,在報刊上揮洒思緒。《獨立評論》及《大公報》成為他們喚起國魂抵抗侵略的主戰場。面對日寇在東北任意肆虐甚至扶植傀儡的暴行,胡適認為政府亟須調整對日方針,“現在滿洲偽國的招牌已撐起來了,日本軍閥和浪人已在那偽國的影子底下實行統治滿洲了”,“此時若再不確立對日外交的方針,若再不肯積極謀外交上的挽救方法,將來隻有於我更不利的情勢”。較之乃師理性冷靜的文風,傅斯年的筆鋒則滿是毫不客氣的火藥味。針對當時全國上下仍沉醉在“醉生夢死”的苟安狀態中,傅對現實進行了無情揭露:“我們且看看所謂北平社會:一群群軍閥官僚、學閥學棍、土棍地痞、無賴青年男女摩登,花他們搶來摸來要來的錢住著”,“試看自北海公園到先農壇,哪裡有國難的氣味?走遍五城的大街小巷,哪裡有憂國的聲息?聽聽人們的談吐,哪一個想到東北的失地?”為何人們面對國恥國難,竟會這樣無動於衷?傅分析道,這主要還是由於國人那些“靠天活著的心理,毫不振作的生活,做順民或逃之夭夭的幻想,知命的哲學!”傅不禁慨嘆,“以今日之局面比宋明亡時真正再像也沒有了!”傅警告那麼些麻木的國人,如果照此下去,做亡國奴的那一天實在不遠了!
1932年秋,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題為《“九·一八”一年了!》的紀念文章,認為九一八事變是“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國難”。無獨有偶,就連向來以政治立場溫和著稱的《大公報》,這時也公開發表“社評”指出:“(日本)充其野心,直欲滅我全國,奴我全民,中國當局者,縱欲屈辱妥協,苟安旦夕,已決非日閥所許”,基於此觀點,“社評”呼吁“四萬萬中國國民”立即行動起來,制止國共內戰,“鞭策政府,俾得悉移‘剿共’之兵力財力,以度此空前非常之國難,此真愛國志士所當劍及履及求其實現者也”。
知識界之所以形成如此高度共識,就在於他們深刻認識到:九一八事變不單是近百年來東亞歷史上最大的一個轉折,也是20世紀以來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三件全球大事。從此,長達十四載的抗日戰爭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從此,中國逐漸升級為世界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從此,“走向抗戰”也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必然選擇。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文史部、北京市委辦公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