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能使群體記憶升華為國家記憶、社會記憶,甚至使民族記憶成為世界記憶——
紀念史學:中共黨史研究的新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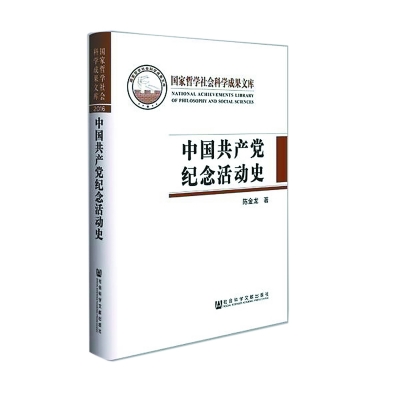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紀念活動史》,陳金龍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紀念是舉行儀式、保存記憶、傳播象征的行為活動,是歷史的一種書寫,歷史通過紀念來表達,歷史因紀念而精彩。陳金龍教授新著《中國共產黨紀念活動史》是一部通過中共紀念活動的拾遺、挖掘、梳理、總結來呈現中共歷史面相的力作。該成果既是中共紀念史學研究的奠基之作,又是中共專門史研究的重要開辟﹔既是中共新文化史研究的有益探索,又是中共記憶史研究的重要起點。
紀念史學研究已然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紀念史學是近年來學界高度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有人指出,紀念只是歷史的腳注,是邊角料。其實不然,中共紀念活動史所呈現的歷史主線並非簡單的歷史題注,而是歷史正題。中共的紀念活動,是一種政治儀式,是利用紀念對象舉行紀念儀式、保存歷史記憶、傳播政治象征、進行政治動員、促進政治認同、引領政治發展的政治活動。
當下,中共紀念史學研究在國內日益受到關注並展開了廣泛研究。陳金龍教授是中共紀念史學研究的最早提出者,也是研究的集大成者。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學界展開了中共紀念活動史研究的熱潮。這些成果中既有把中共紀念活動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的,如《略論民主革命時期中共紀念活動》、《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紀念活動探析》、《中共領導開展紀念活動的基本經驗》等﹔又有把中共某個具體紀念活動作個案研究的,專著有魏建克的《文本話語與歷史記憶——1921-1951年中國共產黨的“七一”紀念》、羅福惠和朱英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等。中共具體紀念活動研究的論文成果最多,涉及中共紀念活動實踐中一些重要紀念,如五一紀念、五四紀念、七一建黨紀念、孫中山紀念、毛澤東紀念等等。可見,中共紀念史學研究已然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中共紀念活動史研究在詮釋老課題做出新水平、用新課題拓展新領域等方面,承載著更多的研究意義
《左傳》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記》有雲:“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論語》名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沒有儀式和象征,就沒有國家。中國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各種紀念活動,世界各國也離不開各種紀念活動。任何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個人等都有自己的紀念活動,紀念活動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承載著傳承歷史的重要價值。
有學者指出,黨史研究的客體決定了它必須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把老課題做出新水平、新境界,用新課題拓展新領域,深化以往的認識。中共紀念活動史研究則能詮釋中共黨史研究的老課題新水平、新課題新領域,承載著更多的研究意義。比如,早期革命期間,中共對廣州起義的紀念規格與十月革命的紀念規格相同,稱之為中國的十月革命道路,這是一種革命理論的建構。通過這樣的紀念,把廣州起義的歷史意義提升為俄國的十月革命道路。可見,紀念不僅提升了事件本身的歷史價值,而且還可以使之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列寧曾經說過,“慶祝偉大革命的紀念日,最好的辦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還沒有完成的革命任務上”。在對於五四紀念活動上,1939年,毛澤東在《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兩篇紀念文章中就通過對五四的紀念的闡釋,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對象、性質、動力、方向以及前途等。五四紀念則成了毛澤東建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重要契機。這也是為什麼說五四紀念的意義遠大於五四事件本身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見,將中共紀念活動史作為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專門史研究方向則“理所當然”。
該書通過將中共各類具體紀念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梳理總結出中共紀念活動的緣由、類型、特點、方式、作用、影響等,揭示出中共紀念史研究的一般規律和方法,是中共紀念史總體把握的一次嘗試,開辟出了中共黨史研究的新領域。
紀念活動是保留民族、國家、政黨歷史記憶的重要途徑,是“新文化史”研究和關注的焦點
“新文化史”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出現的史學新思潮。在新文化史思潮的影響下,中共黨史研究逐漸走出了一條由政治史到社會史再到新文化史的路徑。紀念碑、紀念林、紀念雕像、領袖肖像、紀念廣場、紀念館、紀念日、紀念物等所謂歷史碎片,看似邊緣、非主流,遠離歷史中心,其實是一種軟權力,是歷史的線索。對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稱之為一種民族想象,沒有什麼比無名戰士的紀念碑和墓園,更能鮮明地表現現代民族主義文化了。紀念儀式的操演、歷史記憶的打造、政治象征的運用,與紀念活動的開展緊密相關。該書除了對中共紀念活動進行整體把握考察研究,還分章節專門具體深入研究了經典作家紀念、十月革命紀念、五一紀念、辛亥革命紀念、抗日戰爭紀念、七一紀念、十一紀念等,一定意義上除了厘清中共專門具體紀念活動的歷史脈絡外,還對紀念活動之外所呈現的符號意義和象征意義進行思考。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五一、七一、七七、九三、十一等紀念符號本身就發展成了一個重要政治符號,其傳播和影響遠遠大於其本身。總之,在紀念活動中,中共都會根據現實發展需要,借助紀念對象舉行紀念儀式,打造紀念空間,形成紀念符號,營造紀念場域,傳播紀念象征,實現紀念價值。中共紀念活動史所蘊含的紀念儀式、紀念空間、紀念符號、紀念場域、紀念象征、紀念價值等都是新文化史研究和關注的焦點。
本書很好地詮釋了中共紀念活動對於保存歷史記憶的重要意義。作者指出,歷史記憶的保存需要借助符號、紀念設施,符號、紀念設施支撐歷史記憶。中共在組織紀念活動的過程中,修建紀念設施,制作紀念符號,成為歷史記憶的載體。紀念活動是保留民族、國家、政黨歷史記憶的重要途徑。中共組織開展的紀念活動,強化了與紀念對象相關的歷史記憶。無論國際共運重要任務、事件、節日紀念,還是近代中國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紀念,抑或中共歷史人物、事件、節日紀念,經歷循環、強化之后,已銘刻在民眾的記憶之中,成為不忘的歷史。紀念能使群體記憶升華為國家記憶、社會記憶,甚至使民族記憶成為世界記憶,這正是紀念活動的價值所在。
(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