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文版編譯史述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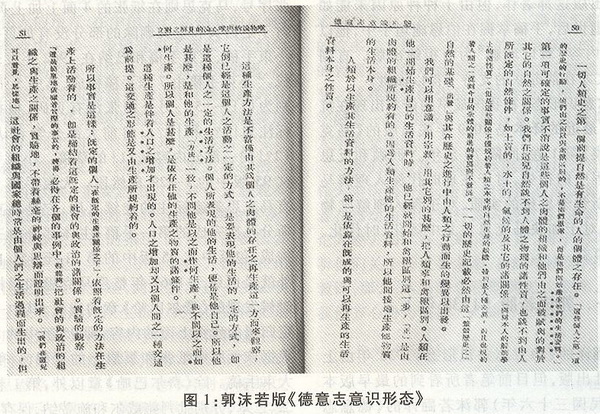 |
《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寫的,它是馬克思主義形成時期的重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然而,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卻是歷經磨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曾做過很多的努力,“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社”,但“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再度打算出版這部著作,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恩格斯逝世后,手稿掌握在伯恩施坦手中,他以“沒寫完”和內容“難以理解”為由拒絕出版。直到1932年,全文才在前蘇聯的支持下得以面世。
《德意志意識形態》在我國最早的譯本出現在抗日戰爭時期,最近的譯本是2009年底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間隔70余年。[1]回顧和反思中文編譯歷程中的得失,對於在現時代深入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思想的實質,對於深入理解唯物史觀的真諦,對於加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當屬有益。
一、郭沫若版(1938年)
郭沫若翻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但目前筆者所看到的最早版本是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郭沫若翻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2],該版作為“沫若譯文集之五”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刊行。
在介紹郭沫若版之前,還應先說明原始手稿的情況,以便統一下文所涉及的關鍵術語。限於篇幅,我們以《費爾巴哈》章為重點展開討論。保存下來的《費爾巴哈》章手稿都寫在“紙張(Bogen)”上,所謂紙張是沿中心線對折為兩頁(Blatt)、包含正反4面的大開紙。恩格斯在每張“紙張”的首頁上標注了紙張序號,馬克思則在紙張的4面上加上頁碼序號,但對於空白頁和全文刪除的部分沒有加頁碼。手稿由小束手稿、大束手稿和巴納在1962年發現的殘頁構成。[3]小束手稿由7張手稿構成,其中5張有頁碼,分別為{1}—{5},另外兩張沒有頁碼,根據國際慣例標注為{1?}和{2?},目前大部分學者認為{1?}和{2?}的一部分內容是{1}的草稿。小束手稿包括中文95版中的1—29自然段。大束手稿17張,其上有馬克思筆跡標注的連續頁碼,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幾次完成的第一手稿,主體部分由三部分手稿構成,包括中文95版中的第31至151自然段。另外就是巴納於1962年整理馬克思和恩格斯遺稿的時候發現的《費爾巴哈》章的殘頁,其中一個無法確定歸屬的殘頁上面的內容,即95版中的30自然段。根據該頁所用紙張和頁眉上的頁碼,一般把它歸於大束手稿。除《費爾巴哈》章以外,第1卷還包括第二、三章,分別批判鮑威爾和施蒂納,保存下來的第2卷手稿中還有第一、四、五章。
郭沫若翻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僅僅是《費爾巴哈》章,他依照的底本是1926年梁贊諾夫編纂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當時還缺少巴納發現的殘頁。郭沫若譯出了《編者導言》的大部分,他大致遵循著梁贊諾夫的編輯原則,其中包括:區分原始手稿和謄清稿﹔遵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上編制的頁碼順序﹔用括號標出小字來表示馬克思和恩格斯涂改或刪除並將其恢復到正文中﹔出於馬克思手筆的訂正、旁注或標識則在腳注中加以說明﹔對於有疑問的判讀和文句不明確之處都用“?”標明﹔對於原稿的缺損和佚失在腳注中說明等等。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筆跡的差別和推斷,郭沫若也沿襲了梁贊諾夫的“口述筆記說”,即馬克思口授,恩格斯記錄,從而形成手稿。由於郭沫若版是新中國成立之前翻譯並刊行的,因此按照當時的書寫習慣以豎排繁體的形式刊印(如圖1)。

郭沫若所依照的梁贊諾夫版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該版本雖然試圖按照手稿的原貌來發表,“將手稿中的文字如實地排成鉛字”,但是沒有能夠科學地處理手稿中的一些片斷,被刪除的部分未能全部恢復,特別是恩格斯的修訂沒能復原,因此邏輯上不夠清晰,形式上不夠完整,不利於閱讀和領會內容的主旨。另一方面,梁贊諾夫在對原始手稿字跡的判讀上還存在錯誤,對手稿的結構未能充分展開研究。
郭沫若翻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初衷是適應當時的革命形勢,給中國讀者提供一個可閱讀的文本,而非供學術研究之用,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做了一些改動。其一,“無關宏旨的廢字、廢句以及腳注,則多半略去了”。因為文中插入修改的文句對於閱讀者來說極為不便,標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筆跡“亦覺不厭其煩”。其二,郭沫若認為,這種校勘學研究如果不針對原始手稿本身是沒有意義的,而對於原文的判讀尚有存疑之處,因此,希望原稿能夠以影印件的形式刊出。其三,梁贊諾夫的《編者導言》中附有“原始手稿與文本的編輯工作”,郭沫若認為這一部分內容“對於讀中文譯書的讀者無甚必要”,因此略去未譯。[4]可見,文獻學意義上的信息在郭沫若版中已經開始丟失。
如果說梁贊諾夫版是試圖忠實地反映《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的最初版本,那麼,郭沫若版就是在中國的第一次嘗試,其文獻價值是巨大的,但限於歷史條件,這個版本的影響不大。郭沫若先生在該譯本脫稿時回憶道,“十年前在日本時我已經買到德文原書,內容要多到二十倍以上”,他當時還看到了3種日文譯本,他非常希望《德意志意識形態》有完整的中文譯本,並且認為,“那在馬昂主義研究上應該是極大的一個貢獻”[5]。
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
郭沫若的“希望”很快就成為現實,1960年,《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完整”版本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中發表。該卷的《編輯說明》明確指出,該版本是譯自“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譯的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參照的是1932年阿多拉茨基主持編纂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正文部分,載於MEGA1第1部門第5卷中。我國1960年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目錄與俄文版完全相同。
這個版本對原始手稿的字跡進行了重新辨認和判讀,修正了梁贊諾夫版中的判讀錯誤,並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上的修改過程通過“異文”說明的方式單獨列出。在隨后的30年間,阿多拉茨基版一直被看作是德文原文的權威版本以及所有其他譯本的底本,未受到任何挑戰。但是這一版本未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當做學術研究的對象,而是為了給大眾提供一個更普遍、更易接受的和系統闡發唯物史觀的版本。就保存下來的原始手稿來說,阿多拉茨基版是“完整”的版本,它既展現了邏輯的完整,又展現了現存內容的完整,也是劃時代的。
中文1960年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編者在文末的注釋中對《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寫作時間、出版情況、編輯原則做了簡要說明。原始手稿上並未標明這部著作的標題,也沒有第1卷和第2卷的標題,這是編者根據馬克思寫作的《駁卡爾·格律恩》這篇論文后加上的。對一些典故、術語、刊物和重要問題也在“注釋”中加以說明﹔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作中引用的著作和文章也在注釋中做出相應說明。例如,編者認為,第2卷第五章“是赫斯起草的,魏德邁抄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校訂的”[6],但並沒有提供考証的細節和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費爾巴哈》章,這一章並未按照梁贊諾夫主張的“歷史考証版”一般原則和通常要求進行編輯,而是阿多拉茨基根據自己的理解“重構”了《費爾巴哈》章,原編者阿多拉茨基認為,原始手稿中的邊注、插入文字和符號等標記就是編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路標”,他還利用手稿右欄中的邊注重新擬定了許多標題,該版還刪除了梁贊諾夫版已經發表過的馬克思寫在手稿最后的“札記”,即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的第135—151段,使這一章看起來更像一部邏輯嚴整的著作。正文僅收錄了改定的文字,對於原始手稿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加寫、改寫、刪除、邊注、插入文字等,阿多拉茨基有選擇地用腳注的形式標出。
實際上,這樣的編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手稿相比出入很大,特別是其中的《費爾巴哈》章。第一,除“一”和“A”標題外,其他標題都是阿多拉茨基加上的。這些標題有的來自手稿右欄中馬克思或恩格斯寫的“邊注”或“插入語”,如“交往和生產力”、“關於意識的生產”、“交往形式本身的生產”等等,有的則是編者根據內容添加的﹔第二,許多原始手稿中正文的內容看起來與上下文缺乏嚴密的邏輯關系,就被編入腳注中[7],未被用作標題的邊注、插入語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手稿的補充也編在腳注之中﹔第三,有選擇地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原稿上刪除的內容以腳注的形式加以整理和編輯,編者認為不重要的刪除和修改則未能刊出﹔第四,隨意打亂原始手稿的排列順序,根據內容的相關程度加以整合,將相連的自然段落分置於各處排列,也就是說,原始手稿的頁碼順序並未按照馬克思編寫的1—72的頁碼順序排列,被徹底打亂,甚至同一頁手稿中的內容被分別放在幾處。[8]例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原始手稿第[9]大張中的內容是四個具有邏輯關聯的自然段落,即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的52、53、54、55段,這四個自然段被俄文版編者分別放在不同位置。
阿多拉茨基這種“拼圖”式的編輯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手稿“面目全非”,導致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敘述的內在邏輯被人為破壞,因此國際上通常稱這個版本為“偽造”版。同時,由於未能區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筆跡,《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分擔問題就被這一版本掩蓋或抹煞了。正是這個版本直接影響了中文譯本,而1960年的中文版本事實上也完全保留了阿多拉茨基版的內容和形式。1972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的這個版本編輯的。
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
1962年,巴納在整理馬克思和恩格斯遺稿的時候發現了兩個《費爾巴哈》章的殘頁,同年就發表在《社會歷史國際評論》雜志第7卷中,中文版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中發表了這個片斷。這兩個片斷的主要內容一是“‘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而不是思想活動”﹔一是“在實踐中,即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質’協調一致”[9]。這樣,1960年版的《費爾巴哈》章就是不完整的。與此同時,阿多拉茨基的編輯原則和方法也在20世紀60年代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質疑。這些新問題促使人們重新去探索《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本結構。
1965年,蘇聯學者巴加圖利亞在《哲學問題》雜志上發表了《費爾巴哈》章的新版本,這個版本的最大特點是恢復了大束手稿的頁碼順序,將巴納發現的殘頁歸入大束手稿,根據恩格斯或伯恩施坦的標注,將小束手稿順序排在大束手稿前面,因此,《費爾巴哈》章的正文有了全新的結構安排,並區別於以往的所有版本。除《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序言》外,巴加圖利亞的新編俄文版單行本將手稿分為四個部分26個小節,僅《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這一節是原始手稿中的標題,其他均為編者依據邊注或對內容的理解而擬定的。1966年,《德國哲學》雜志第4期用德文發表了《費爾巴哈》章,其編排方式與巴加圖利亞版相同,保留了四個部分的劃分,不同的是新德文版隻保留了手稿上原有的標題,刪除了巴加圖利亞所加的其他標題。
1981年,《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第3期首先編譯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第一章的新版本,1985年出版的《馬恩列斯研究資料匯編(1981年)》轉載了這一文章。該版本按照巴加圖利亞的編輯方針編排,同時基本上維持了1960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譯文。1988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這一單行本。首先,這個中文版本所依據的底本是1966年的新德文版,中文版也在正文中刪除了俄文版編者所擬定的25個標題,保留了四個部分的劃分方式,同時將俄文版的標題作為附錄發表﹔其次,這個中文版本在《出版說明》中增加了《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形成過程的簡要說明,將原稿中刪除的部分、馬克思或恩格斯寫下的邊注等等都在腳注中加以說明,還以“手稿的最初方案”的形式在腳注中標出一部分原始手稿上的修改[10]﹔最后,這個中文版本對譯文進行了重新修訂,對於一些重要的術語,如交往(Verkehr)、部落(Stamm)等在注釋中加以說明。總體上看,它不代表對原有中譯文的根本性顛覆,基本思想觀點的表述與前譯文是一致的,該譯文一直沿襲至今。
1995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收錄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費爾巴哈》章。這個版本與1988年的單行本基本相同,只是在腳注中保留了“刪除”和“邊注”,而手稿上的修改僅保留了一處,其他的“手稿的最初方案”都沒有列出。這也是目前發行最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中文譯本,是這一類版本的代表。2003年,我國又出版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這個版本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序言、《費爾巴哈》章以及第1卷第二、三章和第2卷的部分段落,除“真正的社會主義”外,編者根據選編的內容擬定了標題,並按照內容歸類編排,沒有採用原書的順序,該版本還根據德文版對個別譯文做了校訂。2009年,10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又收錄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的序言和《費爾巴哈》章、第2卷的序言“真正的社會主義”,個別譯文也做了修訂。
從1960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的“變化”是顯著的、有目共睹的,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中文版編輯者未能對這種顯著的“變化”給出學理上的說明與詮釋。例如,關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時間,1960年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注明的是“真正開始寫作是在1845年9月”,“於1846年夏初就基本結束了”,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則注明“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寫”,還有一種說法是,“現在可以確定,寫作時間不象從前人們所認為的是9月,而是1845年11月”[11]。這幾種說法涉及的關鍵問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是否與《維干德季刊》第3期有關,這決定著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契機、階段和直接思想資源,直至2009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也未能給出明確的說明。另外,我國學者侯才曾針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中文譯本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對我國編譯出版影響最大的是前蘇聯巴加圖利亞的新編俄譯本,但其中也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因而侯才提出《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文稿結構重建的“方法論原則”以及“重建的概念排列和邏輯線索”[12]。
四、漢譯廣鬆涉版(2005年)與漢譯梁贊諾夫版(2008年)
2005年,南京大學張一兵主持編譯了日文廣鬆涉版《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廣鬆版還附有德文,中文譯本保持其原樣刊出。這對於我國學術界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貢獻。廣鬆涉的編輯方針是:
本版採取的是以一眼就能看清手稿中每頁的狀態(包括刪除、修正、增補、筆跡、欄外筆記等等)的形式印刷,同時以能夠直接反映手稿的內在構成(大小束手稿之間的關系、欄外的增補文章與原來的文章的呼應關系)的方式進行排列的方針。[13]
由此可知,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廣鬆版的特色體現在編和排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編連。巴加圖利亞版和我國1995年的選集版都把小束手稿全部排列在大束手稿的前面,並且小束手稿按照每張紙上的頁碼順序排列,廣鬆涉認為這樣編排不利於把握《費爾巴哈》章的內在邏輯,在廣鬆看來,小束手稿並非馬克思重新寫作的開頭,而是大束手稿的一個修改稿。因此,廣鬆版以大束手稿馬克思標注的頁碼為基本順序,把小束手稿的頁碼順序打亂,按照內容的相關度,分別插入到大束手稿的各個段落之間,重點是注意填補原來大束手稿中被認為缺失的部分,以及處理與大束手稿內容相似的“異稿”。日本學者內田弘曾專門論証廣鬆版編連的思路是最優越的。然而這樣的編連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手稿的內在邏輯,但主觀猜測的成分很大,通常被認為証據不足。
另一方面是排版。廣鬆版按照原始手稿形狀分左右兩欄,左欄為正文,片斷、異稿和謄清稿等排在右欄,廣鬆版還用各種符號標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強調、刪除、增補、加寫和改寫等,基本上再現了手稿的刪改過程,使讀者一目了然,讀者可以在閱讀文本的同時直觀地理解文本的內容。漢譯廣鬆版用楷體和宋體區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筆跡,清晰地反映了兩位作者筆跡的區別,讀者可以據此思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形成過程中各自的作用,日本學界也因此形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比較研究的成果。廣鬆版還較為科學地處理了欄外增補的句子、注釋、索引以及備忘錄等。廣鬆涉的排版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還由此形成了一個流派,1994年英文劍橋版和1998年的日文澀谷正版都屬此類。漢譯本還將廣鬆涉的原注在頁邊刊出,將1998年日本的澀谷正版所新發現的一部分信息在“中譯者注”中刊出。但是在“異文”問題的處理上,正如日本學者大村等人指出的,廣鬆版所依據的是阿多拉茨基版,但阿多拉茨基版並不是權威的、標准的版本,特別是廣鬆沒有參照《費爾巴哈》章的原始手稿,這使得廣鬆版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盡管如此,廣鬆版在學術史上仍然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對后來的研究(包括澀谷版在內)產生了深遠影響,廣鬆版提出的“編”和“排”的問題,對於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成立過程以及唯物史觀最初明確的表述都具有啟示作用,廣鬆版提供的筆跡、刪改等信息是中文1960年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和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無法展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漢譯廣鬆版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漢譯廣鬆版出版以后,我國出現了一個《德意志意識形態》文獻學研究的高潮,中國學者之間、中日兩國學者之間、日本學者之間的學術爭論此起彼伏,客觀上實現了推進學術研究的效果,這裡不再贅述。[14]
2008年,夏凡編譯的《梁贊諾夫版〈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國第二次編譯梁贊諾夫版。這次編譯將郭沫若故意遺漏的內容盡行恢復並譯為中文,尤其是梁贊諾夫在《編者導言》中關於“原始手稿與文本的編輯工作”這一節的內容,使中國讀者看到了完整的梁贊諾夫版。2010年9月,南京大學出版社又編譯和出版了韓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鄭文吉1990年以來主要文獻學研究成果的文集,即《〈德意志意識形態〉與MEGA文獻研究》一書。這本文集可以幫助我們從總體上把握歷史上有關《德意志意識形態》文獻學的爭論,包括戈勞維娜的“季刊說”在內的典型觀點[15],以及鄭文吉本人的研究結論。總之,漢譯廣鬆涉版、漢譯梁贊諾夫版以及鄭文吉的文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撐深入的學術研究。
五、一點啟示
《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特別是《費爾巴哈》章的手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反復修改、刪除、補充、謄抄的,他們生前沒能完成這部著作,更沒有公開發表,因此並無權威的原始版本。同時,手稿沒有連續和完整的頁碼順序,由於保存不善還出現了手稿的殘缺和佚失,因此,對於存在語言障礙的中國讀者來說,如何編譯和理解這部重要著作就成為一個晦澀難解並且見仁見智的學術問題。我國編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歷史反映出來的實際情況是,編譯部門沒有足夠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的第一手資料的照片或影印件,我國也幾乎沒有文獻考據和辨識方面的專家學者,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開展真正意義上的文獻考據研究。於是,編譯部門所參照的底版中的缺點和不足也保留在中文譯本中,這是件令人遺憾的事。縱觀我國編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歷程,我認為可以得到一點啟示:獨立的文獻學研究至為重要。
第一,重視“附屬材料卷”(Apparat)的編譯是深入研究的前提,這也是MEGA2不同於以往版本的獨特之處,所謂“歷史考証”的含義就體現在附屬材料卷中。限於篇幅,這裡僅舉兩例。(1)校勘表(Korrekturenverzeichnis)介紹的是編者在研究和考訂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時發現的筆誤和印刷錯誤,及其更正的情況,它直接影響讀者對於原文的理解。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施蒂納時使用的是1844年奧托·維干德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當年的排版時漏掉了“我[並非]是空洞無物意義上的無,而是……”一句中的“並非”(nicht),導致意思完全相反,而中文1960年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未做說明。這是否會引發馬克思和恩格斯誤讀施蒂納呢?唯有獨立、深入地去研究才能回答。(2)注釋(Erlaeuterungen)是根據國際學術界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研究的成果編撰的,其中包括歷史事實的考據、當時黨派團體的簡介、各種思潮的評述、基本術語和概念的詮釋、各種歷史典故、馬克思和恩格斯引証文獻的出處和源流等等。這對於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意義非凡。但是,如果不先行從事有關研究,如果沒有長時間的學術積澱,不可能編寫出高質量和有價值的“校勘表”和“注釋”。MEGA2有關編輯整理(校勘表)、寫作背景(注釋)、修改過程(異文一覽)的說明對於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頗有裨益,但對非德語國家的讀者來說極為不便且不易翻譯,即便如此,我國學者也應以“輔助讀本”的形式,有選擇地編譯其中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考証信息和結論。它一方面可以使更多的研究者進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語境,另一方面,相關的研究成果又可以提高編譯的質量,從而形成良性互動。
第二,關注國際學術界編譯經典著作引發的新問題有利於深入領會馬克思主義的實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應該是供研究工作者進行研究所使用的版本,否則沒有必要根據MEGA2重新編譯,隻需再版即可。這裡以《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編連問題為例。“編連”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編譯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和“排版”問題同等重要而且恰恰又是難於處理的問題。各版本的巨大差異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對於手稿筆跡的判讀及排版可以盡量做到客觀,而“編連”問題彰顯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准確表述唯物史觀,它是對無形的思想的把握和理解,其難度可想而知,MEGA2遲遲不能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卷的根本原因就是“編連”而非“排版”。2004年MEGA2先行版是按照寫作時間排序,作為一個權威的、正式的、供研究的版本,MEGA2的編輯方針無可厚非。MEGA2並不追求邏輯的嚴整和形式的完善,而是盡可能地追求歷史的客觀和真實。這對於學術研究來說是最為可靠的資料。但如果從“編連”的角度看,2004年MEGA2先行版按照寫作時間排序的編輯方針不是爭論的終點,恰恰相反,它是新研究的起點和工具,關鍵在於研究者如何開展個人獨立的學術探索。因此,必須以MEGA2為基礎,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有目的的取舍過程中再現他們思想發展和反復的過程,利用手稿中的加寫、改寫、未完成的段落、欄外增補以及注釋等信息去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作手稿時的思想發展和變化並且為“編連”提供証據。實際上,這類文獻訓詁和考據意義上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在中國有相當長的歷史淵源,有相當深厚的學術積澱,因此,隻需要創造必要的條件,我國學者就能夠開展獨立的、學術層面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第三,編譯國外主要研究成果,公開編譯部門的部分資料是形成嚴謹學風和產生扎實成果的重要保障。一項真正的學術研究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和對待以往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突破。實際上,國外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很多,包括《MEGA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年鑒》、《馬克思故居文叢》等,我國多年來也有《馬列著作編譯資料》、《馬列主義研究資料》、《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等等,其中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或有關文獻的試譯稿,有關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背景資料、文獻考証、國外學術動態等,馬克思恩格斯提及或批判的人物與流派及其相關資料、國外重要期刊上的譯文等等,是非常有價值的學術和文獻資料。可是仍有許多重要的文獻沒有及時譯為中文,許多中譯文也隻限於“內部參考”,從而限制了這些文獻的功效。因此,目前除繼續編譯國外最新研究外,我認為應盡快公開這些“舊”資料,也可以專題的形式結集出版,從而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參閱這些資料。
總之,我國《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編譯史可分為三個階段:(1)郭沫若版階段﹔(2)1960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與1995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版階段﹔(3)2005年至2008年漢譯版階段。第三階段的編譯方針轉向學術化,也是向第一階段郭沫若版的回歸。
從1938年郭沫若第一次翻譯刊行梁贊諾夫版《德意志意識形態》到2008重譯梁贊諾夫版,似乎回到了起點,但這個起點已經是充滿具體的豐富性的起點,在這個起點上已經收獲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新思路、新方法。目前,在我國形成獨立的文獻學研究氛圍至關重要。巴加圖利亞在1965年曾經說過,“盡管從它的第一章發表至今已有40多年,從《形態》的完整出版至今已有30多年,我們還不能說這部著作的內容和意義已經被完全弄清楚了”。至今又一個40年過去了,我們仍然不能說“完全弄清楚了”[16]。為了給中國讀者提供一個更為可靠的中文譯本,針對原始手稿的文獻學研究無論如何都是不能被遮蔽的,而這種研究如果不是獨立的就不能走得更遠。
注釋:
[1] 目前,國外關於《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完整版本不多,主要是德文、俄文、日文和英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其中的《費爾巴哈》章已經有多種不同的版本:梁贊諾夫版(1926年)、郎茨胡特/邁耶爾版(1932年)、MEGA1(1932年)、巴加圖利亞新俄文版(1965年)、新德文版(1966年)、MEGA2試刊版(1972年)、日文廣鬆涉版(1974年)、英文阿瑟版(1976年)、英文劍橋版(1994年)、日文澀谷正版(1998年)、小林昌人補譯版(2002年)以及MEGA2先行版(2004年)等等。
[2] 郭沫若先生在該書《序》中指出,這個版本是他在20年前,即1927年完成的,他將譯好的手稿交給神州國光社的王禮錫先生,但由於戰亂,未能付梓。抗戰期間,神州國光社將其印出,但郭沫若在“大后方”,一直未能見到這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的編者也曾指出,“《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費爾巴哈》部分,在我國曾有郭沫若同志的譯文,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741頁)遺憾的是,筆者無緣,至今未能得見這一版。1942年7月,上海珠林書店出版了周建人(署名為“克士”)翻譯的《費爾巴哈》章,書名為《德意志觀念體系》。
[3] 為了研究和敘述方便,本文將採取“自然段標注法”,即根據我國1995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所劃分的自然段順序標號(“費爾巴哈”章共計151個自然段)。
[4][5]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郭沫若譯,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編者導言、第1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716頁。
[7] 同上書,第33、41、66、69、82、85、87頁。
[8] 同上書,第41、51、77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68、369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19、20、25、33、35、37、39、47、54、58、63、67、69、75頁。
[11]《馬恩列斯研究資料匯編(1981)》,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頁。
[12] 候才:《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文稿結構的重建》,載《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3年第5期。
[13] [日]廣鬆涉:《文獻學語境中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編輯說明第11頁。譯者在這一版中修訂了關於廣鬆涉版“編輯方針”的譯文。
[14] 參見魯克儉:《“馬克思文本解讀”研究不能無視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1期﹔韓立新:《〈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獻學研究和日本學界對廣鬆版的評價》,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韓立新主編:《新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研究》第一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日]大村泉等:《MEGA2〈德意志意識形態〉之編輯與廣鬆版的根本問題》,載《學術月刊》2007年第1期﹔張一兵:《文獻學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的科學立場》,載《學術月刊》2007年第1期﹔夏凡:《〈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結構問題》,載《學術月刊》2007年第1期﹔魯克儉:《再論“馬克思文本解讀”研究不能無視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3期﹔姜海波:《在文本與思想之間——從廣鬆涉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編連問題談起》,載《理論視野》2010年第2期,等等。
[15] [韓]鄭文吉:《〈德意志意識形態〉與MEGA文獻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頁。
[16] [前蘇聯]巴加圖利亞:《〈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手稿的結構和內容》,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6期。
(作者: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