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黨書”的學問——訪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專家楊勝群研究員
人物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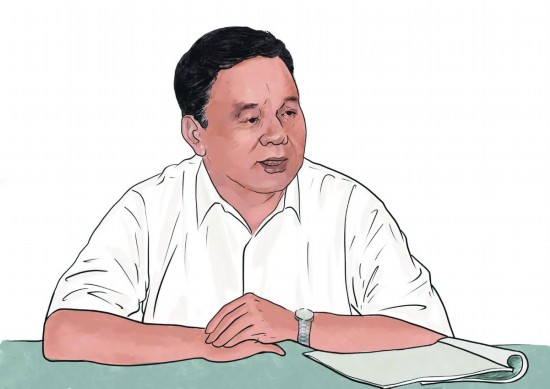
楊勝群(1951— ),湖南華容人,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分配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1984年調湖南省委宣傳部工作,1990年調回中央文獻研究室。長期從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編輯、生平思想研究和中共黨史及黨的基本理論研究工作。曾任《毛澤東文集》副主編,主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毛澤東文藝論集》《鄧小平傳(1904—1974)》《鄧小平年譜(1904—1974)》《鄧小平傳(1975—1997)》等。出版有個人文集。
記者: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並系統闡述習近平文化思想,請從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角度,談一談您的體會。
楊勝群: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全黨的重大政治任務,黨的文獻編輯研究事業是黨的事業重要組成部分,在研究黨的理論、總結黨的經驗、弘揚黨的傳統、傳承黨的作風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於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者來說,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是政治學習、政治要求,也是業務學習、崗位要求。
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是一項政治性、思想性都非常強的工作。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忠實踐行“兩個維護”的政治要求,也是扎實推進工作的重要保証。習近平總書記就黨史和文獻工作有過一系列重要論述,特別是他從黨的歷史和文獻角度深刻闡述了一系列帶根本性、戰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記者: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始於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曾親自組織指導編輯《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等黨的文獻集,並將之稱為“黨書”。您長期從事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對於編“黨書”最重要的體會是什麼?
楊勝群:今天,我們編輯研究黨的文獻,仍可以說是編“黨書”,有明確的黨性要求,或者說是政治性要求,要特別重視和保証編研作品的政治效果。我們編輯出版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老一輩革命家的著作集有兩個目的:一是為全黨政治、理論學習提供基本文本,二是為研究、宣傳黨的歷史提供基本資料。有的讀者問,你們編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選集、文選和其他專題文集,為什麼不收那些存在錯誤的東西?黨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探索前進的歷史,探索中不可避免地發生過錯誤。這也反映在黨的歷史文獻中,反映在毛澤東同志的著述中。今天,我們編輯老一輩革命家的選集、文選、文集等,是要充分發掘和整理他們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寶貴思想遺產,是編輯反映他們正確思想的代表作,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和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對於他們在一些復雜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錯誤,我們採用編纂黨的綜合歷史文獻集加以反映,特別是在編寫他們的年譜、傳記中加以反映。
我們2002年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文藝論集》,其中收了一篇《毛澤東談〈紅樓夢〉》,集納了毛澤東同志1959年到1973年關於《紅樓夢》的幾次談話。書出版以后,有讀者來信問我們為什麼不收1954年毛澤東同志寫給中央政治局的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從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引申到同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有一位學者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說該書沒有收入這封信,總覺得是一個遺憾。為什麼沒有收這封信呢?這不是我們工作的疏忽,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新中國成立后各方面除舊布新,在思想領域清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是必要的。但在這封信中俞平伯關於《紅樓夢》的學術觀點被等同於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受到批判,使圍繞《紅樓夢》的學術批判演變為政治批判,混淆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帶來了非常消極的后果。如果我們把這封信收進書中,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放在一起,再一次公開發表,那就是在肯定信中的觀點,就會混淆歷史上的政治是非。
記者:黨的文獻編研工作在為人們做好解疑釋惑方面是否能發揮重要作用?
楊勝群:文獻編輯研究工作在這方面特別要承擔起澄清社會上一些錯誤流傳的任務。比如,我們都知道對毛澤東和鄧小平曾經流傳一個“正帥”“副帥”的說法,即毛澤東是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正帥”,鄧小平是“大躍進”運動的“副帥”。境外一家出版社還出了一本書,叫《大躍進“副帥”——鄧小平》,國內也有人寫文章說鄧小平是“大躍進”運動的“副帥”。言外之意,“大躍進”運動的錯誤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個“正、副帥”的責任。我們在撰寫《鄧小平傳(1904—1974)》的過程當中,搞清楚了這個“正帥”“副帥”,是1959年4月上旬召開的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叫出來的。八屆七中全會是什麼會?是糾“左”的會,糾正“大躍進”運動錯誤的會,不是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會。毛主席在這個會上是讓鄧小平來當糾正“大躍進”運動錯誤的“副帥”,他自己當“正帥”。毛澤東還對鄧小平說,“你挂帥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這就是所謂毛澤東和鄧小平“正帥”“副帥”的由來。“大躍進”運動的“正帥”“副帥”和糾正“大躍進”運動的“正帥”“副帥”,含義完全不一樣啊!
記者:您的講述透出對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的一種情感因素。
楊勝群:我們長期從事老一輩革命家著作編輯和生平思想研究工作,在對老一輩革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對他們產生了一種由衷的崇敬之情。我經常說,由我們這一代人來編寫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時期的年譜、傳記,是很合適的。為什麼?因為我們當中不少人包括我自己,是恢復高考之后上大學,在改革開放當中成長起來的,我們對改革開放有一種獨特的感受。恢復高考和改革開放都是鄧小平同志決策的,我們對鄧小平同志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每逢紀念恢復高考或者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時候,我們都想編點東西。2007年是恢復高考30周年,我和幾個同志,從收集資料開始,用幾個月編輯完成《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講話談話批示集》,出版之后反響很好,恢復高考改變了太多的人的人生。
記者:情感因素是否會影響歷史研究的客觀公正性?
楊勝群:強調歷史研究工作客觀公正是對的,但實際上研究歷史,不可避免會帶有主觀傾向和情感因素,關鍵在於有沒有正確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古今中外優秀的歷史著作(包括歷史人物傳記)都有鮮明的主觀傾向。中國漢代史家司馬遷在《史記》中褒貶、臧否,態度鮮明,“西方史學之父”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在著作中也是愛憎分明,他們的著作都成為傳世之作。我們描述一段歷史,總要先有一個基本判斷,這個判斷裡面就有我們主觀的愛憎和情感,有我們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如果我們對黨領導人民百年奮斗的歷史,對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過卓越貢獻的領袖人物冷漠無情的話,能編好他們的著作嗎?能寫好他們的年譜、傳記嗎?
記者:黨的文獻編輯和研究工作科學性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勝群: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編輯和生平思想研究同其他哲學社會科學一樣,具有科學性要求。具體來說,一是要確保資料的可靠性和系統性。有人問我,你們撰寫的年譜、傳記同社會上以及境外的一些同類作品有什麼區別?我說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是以大量的檔案資料為依據,用大量的檔案資料說話的,尤其是運用了檔案部門保存的大量內部檔案。如《毛澤東傳》《鄧小平傳》,所運用的內部文件、會議記錄等檔案資料都達數千件。
再就是要有政治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的學術視角和學術視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編輯和生平思想研究有明確的政治性要求,但它最終是科學研究、是學術研究,政治性要求最終要通過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實現。因此工作的全過程要貫穿學術思維。我們有組織地撰寫領袖人物的年譜、傳記,起步是很晚的,西方人寫中共領袖人物的傳記類作品比我們早,也比我們多。他們的很多作品有一個共同的偏見,就是總是從權力斗爭和個人恩怨的角度考察人物關系,有的則過分強調人物性格。而我們則重在寫出人物的思想,寫出人物的思想發展脈絡。寫《毛澤東傳》就要寫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發展脈絡,寫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寫《鄧小平傳》就要寫出鄧小平同志的思想發展脈絡,寫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發展過程。
在黨內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不斷克服必然產生的各種錯誤思想傾向,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鮮明特點和傳統。我們撰寫領袖人物的年譜、傳記等,特別注重在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中考察和揭示人物的思想發展脈絡,凸顯人物獨特的思想和品格,以對歷史作出更具思想性的總結,並給后人提供思想啟示,這是我們的作品重要的學術視角和學術價值。
記者:不回避黨內矛盾、黨內斗爭,是否也意味著不回避領袖人物曾經有過的錯誤?
楊勝群:是的,我們堅持實事求是地分析、評價黨的領袖人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回避錯誤和缺點。比如《毛澤東傳》對於毛澤東同志在反右擴大化、“大躍進”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問題上思想理論和實際工作中的錯誤,不僅沒有回避,而且寫得比較透徹,出版后反響很好,為什麼?因為既充分尊重客觀史實,又有辯証理性的分析,特別是對他犯錯誤的主客觀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這樣,並不損害毛澤東同志作為人民領袖和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崇高地位,也不影響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科學價值。寫《鄧小平傳(1904—1974)》也是這樣,我們對鄧小平同志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有過的錯誤也沒有回避,因為鄧小平同志自己后來也說“這些事我是有責任的”,我們也沒有必要回避。
記者:這項工作的科學性要求,肯定還要體現在作風和學風上吧?
楊勝群:嚴謹精細、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是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的政治性要求和科學性要求所決定的。在著作編輯方面,一篇文稿的整理編輯,各個環節的工作都要嚴謹、細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收錄了鄧小平同志很重要的一篇談話《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篇談話實際上是鄧小平同志1988年兩段談話的集成,一段是9月5日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的談話,另一段是9月12日聽取有關部門工作匯報時的談話。兩段談話時間相隔8天。9月12日的談話中,鄧小平同志明確講道:“我在同胡薩克的談話當中講到科學技術恐怕是第一生產力。”但是,外事部門提供的鄧小平同志9月5日同胡薩克的談話記錄中沒有這句話。編輯組的同志覺得才8天時間,鄧小平同志不會記錯,肯定是談了,我們就刨根究底地查,最后查清楚了。什麼情況呢?鄧小平同志不是在正式會談中而是在宴請胡薩克的談話中講到的這句話。當時擔任翻譯工作的同志非常負責,把這句話記錄下來了,而且登在了《接待簡報》上,所以,正式會談記錄上沒有。參加編輯的同志拿到了這份簡報,如獲至寶,把鄧小平同志這句話同其他有關談話內容一起整理成篇,這樣就有了鄧小平同志《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篇光輝著作和這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的同志不刨根究底,不想辦法查,這篇著作就出不來,這個重要觀點就出不來!
記者:黨的文獻編輯研究工作可以看到對古典文獻學傳統的繼承。
楊勝群:重考辨,這是中國古典文獻學的重要傳統,也是黨的文獻編輯研究的基本功。黨的文獻涉及大量人物、事件及其他各種史料,都要認真進行考訂和辨識。比如《毛澤東書信選集》,收入毛澤東同志各個時期的書信370多封,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他早年寫給家鄉親友的,涉及許多底層群眾和舊時地名。我們在編輯這本書時,對每一封信,對每一個人名、地名都做了考訂、核實。有一位老同志寫了一篇文章《一信之考旬月躊躇:〈毛澤東書信選集〉編輯記事之一》,作了描述。再比如毛澤東同志的《尋烏調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調查報告之一,有專家說《尋烏調查》是那個時代最典型、最翔實的社會學文本,這是要流傳於后世的。全文8萬多字,提到了數十家商鋪、數十個老地名、200多種物產,數十個有名有姓的各色人物。我們在將《尋烏調查》編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時,對這些都做了詳細的考訂,做到了不出一處錯訛。
嚴謹學風體現在撰寫老一輩革命家年譜、傳記上的要求,一是使用材料要可信,半點馬虎都要不得﹔二是分析評論要准確,一點都不能隨意。我們撰寫《鄧小平傳》,寫到1961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要求,鄧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北京順義農村調查公共食堂要不要辦下去的問題。我們原來都聽說過,鄧小平同志在順義說過一句話“辦食堂是社會主義,不辦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但真到要落筆寫的時候,卻不知這句話出自哪個地方。在我們保存的鄧小平文稿檔案裡面都找不到這句話。因此,我們把這句話寫上去又劃掉,劃掉了覺得又非常可惜,不甘心。多好的一句話,非常符合鄧小平同志的性格,體現了辯証法。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在順義縣委組織編寫的《順義縣農業合作化史料》中找到了鄧小平同志講這句話的記載,這才把這句話寫到傳記裡了。這種事例還有很多。有位老同志講,文獻編輯研究工作真是“沒有底”,但是我們又要做到“有底”。什麼叫“有底”呢?就是我們使用的每一條材料,對人物、事件評價的每一個斷語,一定要做到心裡有底、言之有據。
記者:時代在發展,對文獻編輯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您有什麼體會?
楊勝群:還要與時俱進,培養創新思維,提升創新能力。1984年,原文獻研究室主任胡喬木同志提出過一個很重要的意見。他說:最近幾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選的注釋,感到起草這些注釋的同志都有一種通病,就是議論多、斷語多,好像法官做判決一樣。我認為,寫注釋主要是對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況、歷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紹,以幫助讀者理解正文,切忌發議論、下斷語。從那以后,我們對注釋工作做了很大的改進,在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時,對涉及的一些人物包括張國燾等重要人物作注,主要介紹他們的基本情況、生平經歷,基本不作評價,更不下斷語。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編寫領袖人物傳記作品也有明顯創新,我們把人物的政治傳記寫得更豐富、更豐滿、更耐讀了,不僅寫出人物的生平思想,而且努力寫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寫出人物情感活動,展示他們作為常人的一面,讓人物更加鮮活生動、有血有肉。
記者:您從事文獻編輯研究工作,面向歷史,而學術視野總朝向未來。
楊勝群:我們黨在百年的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和珍貴的思想遺產。這些歷史經驗和思想遺產都蘊含在大量歷史文獻中,繼續深入發掘、整理和研究歷史文獻,仍然是我們的重要任務。我們黨還在不斷前進,黨的事業還在不斷發展,新的文獻還在不斷產生。黨的文獻編輯研究永遠是一塊沃土,需要和值得一代代人去耕耘。
(本刊記者 海 兵)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