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投降迄今已80年,但中日歷史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正視“戰爭記憶”:為中日歷史認知尋共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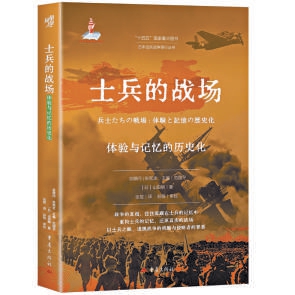
《士兵的戰場:體驗與記憶的歷史化》 山田朗 著 張煜 譯 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
揆諸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無論是靖國神社問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慰安婦”問題,抑或“二戰”勞工賠償問題,均與近代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有關。兩國之間的歷史問題紛爭,很大程度源於彼此對那場戰爭的認知不同,而這種不同的認知,相當大的一部分來自於不同的“戰爭記憶”。
“戰爭記憶”的傳承脈絡與轉化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成田龍一將戰爭樣態的系譜分為以下幾個時期:戰爭作為“情況”而被敘述的時期(1931—1945年)、作為“體驗”而被敘述的時期(1945—1965年)、作為“証言”戰爭而被敘述的時期(1965—1990年)、作為“記憶”而被敘述的時期(1990年以后)。
從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迄今已80年,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人已基本凋零殆盡,這就意味著擁有“戰爭記憶”的那一代人,現在已經成為極少數,作為“情況”而被敘述的戰爭幾乎不再被提起﹔作為“體驗”而被敘述的戰爭話題也逐漸沉寂﹔戰爭“証言”者正逐漸逝去﹔而戰爭作為“記憶”,不僅在中國學界成為了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對象,而且如下所述在中國民間可謂方興未艾。
“戰爭記憶”最為重要的是傳承問題。筆者認為,在“戰爭記憶”傳承過程中,有一個問題不應忽視,那就是社會對“戰爭記憶”內容的理解。關於戰后日本人的歷史觀,李若愚(歷史研究學者)“認為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日本左翼對侵略的反省立場﹔第二類則是試圖通過掩耳盜鈴以湮沒歷史真相的右翼史觀﹔第三類,或許也是持有人最多的一類,便是日本社會大部分老百姓的立場。他們對那段戰爭歷史有著強烈的疏離感、陌生感”。
對於以上第二類的右翼分子,其之所以對那場戰爭抱持右翼史觀,原因不外乎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使然,抑或“戰爭記憶”在轉化為“歷史”過程中的失真。對於前者,學界的批判性研究已是充棟盈車,不再贅述,在此主要談談后者。
《士兵的戰場:體驗與記憶的歷史化》一書認為,“戰爭記憶”在被傳承的過程中,經歷了重構、選擇,最終形成了“歷史”。“戰爭記憶”的傳承,與一般“記憶”的傳承相同,大致可分為私人傳承與公共傳承。私人傳承是個人或家族間傳承的微觀行為,而公共傳承是以教科書記述為代表的宏觀行為。通過個人或家族傳承而來的具有私人性的“記憶”,通常包含許多個別且具體的特殊事例,而后在其所在地區或社會集體中被匯集,成為同代人的共同體驗,這表現為“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可以說是戰爭年代體驗者私人“記憶”群的最大公約數。以“集體記憶”為基礎,建構、敘述而成的產物(教科書等),在學校等社會上流傳,便形成記憶的公共傳承。可以將其設想為以下流程:①私人傳承→②集體記憶→③公共傳承→④“歷史”化。
中日“戰爭記憶”的重視落差
一些學者對李若愚所言的第二類人展開批判,讓人誤解為中日之間的各類歷史問題主要來自於對“戰爭記憶”內容的理解不同,但其實第二類人在日本社會所佔比重並不大,不足以影響中日關系,而真正形成影響的主要是第三類,即社會整體對“戰爭記憶”的重視程度。
具言之,當前中日兩國對“戰爭記憶”的重視程度完全不同。中國每年都會舉辦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以及抗戰勝利等紀念活動﹔初高中的歷史課程以及大學的《近代史綱要》等課程一定會講授相關內容。與此同時,民間的“戰爭記憶”被激活,典型的例子就是無處不在的抗日影視劇。與之相對,日本社會對“戰爭記憶”表現出疏離感、陌生感。即便有學者指出戰后日本的戰爭記憶具有選擇性,即有選擇性的記憶戰爭“受害者”身份,遺忘“加害者”身份,但其在社會中的關注度遠不能望中國社會之項背。兩國社會整體對那段“戰爭記憶”重視程度的不均衡性,才是導致中日兩國之間歷史問題懸而未決的根本性原因。
該書作者山田朗不無憂慮地指出:“日本社會整體的‘戰爭記憶’正不斷淡化。”而山田在另一篇論文中認為,這是因為日本社會“戰爭責任性的展開和歷史修正主義的抬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該書的誕生就是阻止這種“淡化”的趨勢,也就是遏制日本社會歷史修正主義的抬頭,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重構和歷史化需要傳承的‘記憶’”。
為了撰寫此書,作者一共查找了851部戰爭體驗者的回憶錄(單行本),以及逾1100份口述史料,顯示了其寬廣的視野、扎實的研究功底和實証性偏好。正如山田自己所言,這本書是以戰爭體驗者自身記述的“體驗”“証言”,以及體驗者在翻閱公刊戰史或對其進行批判性探討后形成的,以“記憶”為素材,對理應得到傳承的“記憶”群進行重構,對以太平洋戰爭為中心的戰爭進行歷史敘述。因此,我們在閱讀該書的時候,有時會有碎片化之感。
日本當探尋“隱匿的暴行記憶”
該書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提及了未能留下有關戰爭的“體驗”“証言”“記憶”的戰死者:“無法訴說的戰死者和能進行訴說的生還者之間,差別是無限大的,但實際也隻有一線之隔。因為,決定戰場上的生與死,只是‘運氣’而已。在本書中出場的士兵,他們都是因為能夠生還才留下了回憶和証言。”即便如上所述,作者找到了大量的回憶錄和口述史料,但相較於戰爭中數百萬的日軍士兵,這些資料所描繪的“戰爭記憶”不過是一鱗片爪,我們據此來俯瞰戰爭的真實圖景不免有群盲摸象之感,因此我們在閱讀過程中要對此保持警惕。
該書略顯不足之處在於所謂的“深層記憶”。作者認為“深層記憶”是私人傳承容易斷絕的那部分“記憶”,這裡的關鍵詞則是“隱匿”和“施暴”,其主要表現在戰爭暴行及違法行為的“記憶”。
該書也提到了日軍使用毒氣、自殺式攻擊的“特攻隊”,但對日軍在包括中國戰場在內的區域戰爭暴行的筆墨卻不多。當然,作者也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主要源於收集到的回憶錄與口述資料中相關部分的佔比甚少,“往往是戰爭親歷者有無法向家人(尤其是下一代)敘述的事情(殘暴行為等),或者是迫於社會壓力(包括有形或無形的)無法言明的場合”。對此,有學者認為日本社會要探究和傳承這種“深層記憶”,必須克服狹隘的個人立場與民族主義情緒。
(作者為廣西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