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版编译史述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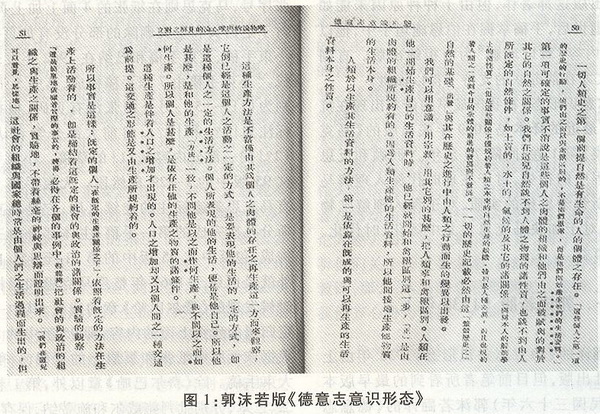 |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然而,这部重要著作的出版却是历经磨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曾做过很多的努力,“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社”,但“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再度打算出版这部著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恩格斯逝世后,手稿掌握在伯恩施坦手中,他以“没写完”和内容“难以理解”为由拒绝出版。直到1932年,全文才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得以面世。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我国最早的译本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近的译本是2009年底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间隔70余年。[1]回顾和反思中文编译历程中的得失,对于在现时代深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实质,对于深入理解唯物史观的真谛,对于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当属有益。
一、郭沫若版(1938年)
郭沫若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但目前笔者所看到的最早版本是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郭沫若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2],该版作为“沫若译文集之五”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刊行。
在介绍郭沫若版之前,还应先说明原始手稿的情况,以便统一下文所涉及的关键术语。限于篇幅,我们以《费尔巴哈》章为重点展开讨论。保存下来的《费尔巴哈》章手稿都写在“纸张(Bogen)”上,所谓纸张是沿中心线对折为两页(Blatt)、包含正反4面的大开纸。恩格斯在每张“纸张”的首页上标注了纸张序号,马克思则在纸张的4面上加上页码序号,但对于空白页和全文删除的部分没有加页码。手稿由小束手稿、大束手稿和巴纳在1962年发现的残页构成。[3]小束手稿由7张手稿构成,其中5张有页码,分别为{1}—{5},另外两张没有页码,根据国际惯例标注为{1?}和{2?},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1?}和{2?}的一部分内容是{1}的草稿。小束手稿包括中文95版中的1—29自然段。大束手稿17张,其上有马克思笔迹标注的连续页码,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几次完成的第一手稿,主体部分由三部分手稿构成,包括中文95版中的第31至151自然段。另外就是巴纳于1962年整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的时候发现的《费尔巴哈》章的残页,其中一个无法确定归属的残页上面的内容,即95版中的30自然段。根据该页所用纸张和页眉上的页码,一般把它归于大束手稿。除《费尔巴哈》章以外,第1卷还包括第二、三章,分别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保存下来的第2卷手稿中还有第一、四、五章。
郭沫若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仅仅是《费尔巴哈》章,他依照的底本是1926年梁赞诺夫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当时还缺少巴纳发现的残页。郭沫若译出了《编者导言》的大部分,他大致遵循着梁赞诺夫的编辑原则,其中包括:区分原始手稿和誊清稿;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上编制的页码顺序;用括号标出小字来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涂改或删除并将其恢复到正文中;出于马克思手笔的订正、旁注或标识则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对于有疑问的判读和文句不明确之处都用“?”标明;对于原稿的缺损和佚失在脚注中说明等等。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迹的差别和推断,郭沫若也沿袭了梁赞诺夫的“口述笔记说”,即马克思口授,恩格斯记录,从而形成手稿。由于郭沫若版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翻译并刊行的,因此按照当时的书写习惯以竖排繁体的形式刊印(如图1)。

郭沫若所依照的梁赞诺夫版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该版本虽然试图按照手稿的原貌来发表,“将手稿中的文字如实地排成铅字”,但是没有能够科学地处理手稿中的一些片断,被删除的部分未能全部恢复,特别是恩格斯的修订没能复原,因此逻辑上不够清晰,形式上不够完整,不利于阅读和领会内容的主旨。另一方面,梁赞诺夫在对原始手稿字迹的判读上还存在错误,对手稿的结构未能充分展开研究。
郭沫若翻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初衷是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可阅读的文本,而非供学术研究之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做了一些改动。其一,“无关宏旨的废字、废句以及脚注,则多半略去了”。因为文中插入修改的文句对于阅读者来说极为不便,标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亦觉不厌其烦”。其二,郭沫若认为,这种校勘学研究如果不针对原始手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而对于原文的判读尚有存疑之处,因此,希望原稿能够以影印件的形式刊出。其三,梁赞诺夫的《编者导言》中附有“原始手稿与文本的编辑工作”,郭沫若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对于读中文译书的读者无甚必要”,因此略去未译。[4]可见,文献学意义上的信息在郭沫若版中已经开始丢失。
如果说梁赞诺夫版是试图忠实地反映《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最初版本,那么,郭沫若版就是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其文献价值是巨大的,但限于历史条件,这个版本的影响不大。郭沫若先生在该译本脱稿时回忆道,“十年前在日本时我已经买到德文原书,内容要多到二十倍以上”,他当时还看到了3种日文译本,他非常希望《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完整的中文译本,并且认为,“那在马昂主义研究上应该是极大的一个贡献”[5]。
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
郭沫若的“希望”很快就成为现实,1960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版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中发表。该卷的《编辑说明》明确指出,该版本是译自“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参照的是1932年阿多拉茨基主持编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正文部分,载于MEGA1第1部门第5卷中。我国1960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录与俄文版完全相同。
这个版本对原始手稿的字迹进行了重新辨认和判读,修正了梁赞诺夫版中的判读错误,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上的修改过程通过“异文”说明的方式单独列出。在随后的30年间,阿多拉茨基版一直被看作是德文原文的权威版本以及所有其他译本的底本,未受到任何挑战。但是这一版本未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当做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为了给大众提供一个更普遍、更易接受的和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的版本。就保存下来的原始手稿来说,阿多拉茨基版是“完整”的版本,它既展现了逻辑的完整,又展现了现存内容的完整,也是划时代的。
中文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编者在文末的注释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写作时间、出版情况、编辑原则做了简要说明。原始手稿上并未标明这部著作的标题,也没有第1卷和第2卷的标题,这是编者根据马克思写作的《驳卡尔·格律恩》这篇论文后加上的。对一些典故、术语、刊物和重要问题也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中引用的著作和文章也在注释中做出相应说明。例如,编者认为,第2卷第五章“是赫斯起草的,魏德迈抄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校订的”[6],但并没有提供考证的细节和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费尔巴哈》章,这一章并未按照梁赞诺夫主张的“历史考证版”一般原则和通常要求进行编辑,而是阿多拉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了《费尔巴哈》章,原编者阿多拉茨基认为,原始手稿中的边注、插入文字和符号等标记就是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路标”,他还利用手稿右栏中的边注重新拟定了许多标题,该版还删除了梁赞诺夫版已经发表过的马克思写在手稿最后的“札记”,即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第135—151段,使这一章看起来更像一部逻辑严整的著作。正文仅收录了改定的文字,对于原始手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加写、改写、删除、边注、插入文字等,阿多拉茨基有选择地用脚注的形式标出。
实际上,这样的编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手稿相比出入很大,特别是其中的《费尔巴哈》章。第一,除“一”和“A”标题外,其他标题都是阿多拉茨基加上的。这些标题有的来自手稿右栏中马克思或恩格斯写的“边注”或“插入语”,如“交往和生产力”、“关于意识的生产”、“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等,有的则是编者根据内容添加的;第二,许多原始手稿中正文的内容看起来与上下文缺乏严密的逻辑关系,就被编入脚注中[7],未被用作标题的边注、插入语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手稿的补充也编在脚注之中;第三,有选择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稿上删除的内容以脚注的形式加以整理和编辑,编者认为不重要的删除和修改则未能刊出;第四,随意打乱原始手稿的排列顺序,根据内容的相关程度加以整合,将相连的自然段落分置于各处排列,也就是说,原始手稿的页码顺序并未按照马克思编写的1—72的页码顺序排列,被彻底打乱,甚至同一页手稿中的内容被分别放在几处。[8]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第[9]大张中的内容是四个具有逻辑关联的自然段落,即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的52、53、54、55段,这四个自然段被俄文版编者分别放在不同位置。
阿多拉茨基这种“拼图”式的编辑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手稿“面目全非”,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叙述的内在逻辑被人为破坏,因此国际上通常称这个版本为“伪造”版。同时,由于未能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分担问题就被这一版本掩盖或抹煞了。正是这个版本直接影响了中文译本,而1960年的中文版本事实上也完全保留了阿多拉茨基版的内容和形式。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的这个版本编辑的。
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
1962年,巴纳在整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的时候发现了两个《费尔巴哈》章的残页,同年就发表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杂志第7卷中,中文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中发表了这个片断。这两个片断的主要内容一是“‘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一是“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9]。这样,1960年版的《费尔巴哈》章就是不完整的。与此同时,阿多拉茨基的编辑原则和方法也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质疑。这些新问题促使人们重新去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结构。
1965年,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章的新版本,这个版本的最大特点是恢复了大束手稿的页码顺序,将巴纳发现的残页归入大束手稿,根据恩格斯或伯恩施坦的标注,将小束手稿顺序排在大束手稿前面,因此,《费尔巴哈》章的正文有了全新的结构安排,并区别于以往的所有版本。除《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序言》外,巴加图利亚的新编俄文版单行本将手稿分为四个部分26个小节,仅《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这一节是原始手稿中的标题,其他均为编者依据边注或对内容的理解而拟定的。1966年,《德国哲学》杂志第4期用德文发表了《费尔巴哈》章,其编排方式与巴加图利亚版相同,保留了四个部分的划分,不同的是新德文版只保留了手稿上原有的标题,删除了巴加图利亚所加的其他标题。
1981年,《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第3期首先编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的新版本,1985年出版的《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年)》转载了这一文章。该版本按照巴加图利亚的编辑方针编排,同时基本上维持了196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的译文。1988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这一单行本。首先,这个中文版本所依据的底本是1966年的新德文版,中文版也在正文中删除了俄文版编者所拟定的25个标题,保留了四个部分的划分方式,同时将俄文版的标题作为附录发表;其次,这个中文版本在《出版说明》中增加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形成过程的简要说明,将原稿中删除的部分、马克思或恩格斯写下的边注等等都在脚注中加以说明,还以“手稿的最初方案”的形式在脚注中标出一部分原始手稿上的修改[10];最后,这个中文版本对译文进行了重新修订,对于一些重要的术语,如交往(Verkehr)、部落(Stamm)等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总体上看,它不代表对原有中译文的根本性颠覆,基本思想观点的表述与前译文是一致的,该译文一直沿袭至今。
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收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这个版本与1988年的单行本基本相同,只是在脚注中保留了“删除”和“边注”,而手稿上的修改仅保留了一处,其他的“手稿的最初方案”都没有列出。这也是目前发行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译本,是这一类版本的代表。2003年,我国又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这个版本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费尔巴哈》章以及第1卷第二、三章和第2卷的部分段落,除“真正的社会主义”外,编者根据选编的内容拟定了标题,并按照内容归类编排,没有采用原书的顺序,该版本还根据德文版对个别译文做了校订。2009年,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又收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的序言和《费尔巴哈》章、第2卷的序言“真正的社会主义”,个别译文也做了修订。
从1960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的“变化”是显著的、有目共睹的,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文版编辑者未能对这种显著的“变化”给出学理上的说明与诠释。例如,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注明的是“真正开始写作是在1845年9月”,“于1846年夏初就基本结束了”,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则注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还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可以确定,写作时间不象从前人们所认为的是9月,而是1845年11月”[11]。这几种说法涉及的关键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与《维干德季刊》第3期有关,这决定着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契机、阶段和直接思想资源,直至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也未能给出明确的说明。另外,我国学者侯才曾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文译本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对我国编译出版影响最大的是前苏联巴加图利亚的新编俄译本,但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因而侯才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重建的“方法论原则”以及“重建的概念排列和逻辑线索”[12]。
四、汉译广松涉版(2005年)与汉译梁赞诺夫版(2008年)
2005年,南京大学张一兵主持编译了日文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广松版还附有德文,中文译本保持其原样刊出。这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贡献。广松涉的编辑方针是:
本版采取的是以一眼就能看清手稿中每页的状态(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迹、栏外笔记等等)的形式印刷,同时以能够直接反映手稿的内在构成(大小束手稿之间的关系、栏外的增补文章与原来的文章的呼应关系)的方式进行排列的方针。[13]
由此可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广松版的特色体现在编和排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编连。巴加图利亚版和我国1995年的选集版都把小束手稿全部排列在大束手稿的前面,并且小束手稿按照每张纸上的页码顺序排列,广松涉认为这样编排不利于把握《费尔巴哈》章的内在逻辑,在广松看来,小束手稿并非马克思重新写作的开头,而是大束手稿的一个修改稿。因此,广松版以大束手稿马克思标注的页码为基本顺序,把小束手稿的页码顺序打乱,按照内容的相关度,分别插入到大束手稿的各个段落之间,重点是注意填补原来大束手稿中被认为缺失的部分,以及处理与大束手稿内容相似的“异稿”。日本学者内田弘曾专门论证广松版编连的思路是最优越的。然而这样的编连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手稿的内在逻辑,但主观猜测的成分很大,通常被认为证据不足。
另一方面是排版。广松版按照原始手稿形状分左右两栏,左栏为正文,片断、异稿和誊清稿等排在右栏,广松版还用各种符号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强调、删除、增补、加写和改写等,基本上再现了手稿的删改过程,使读者一目了然,读者可以在阅读文本的同时直观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汉译广松版用楷体和宋体区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清晰地反映了两位作者笔迹的区别,读者可以据此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形成过程中各自的作用,日本学界也因此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研究的成果。广松版还较为科学地处理了栏外增补的句子、注释、索引以及备忘录等。广松涉的排版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还由此形成了一个流派,1994年英文剑桥版和1998年的日文涩谷正版都属此类。汉译本还将广松涉的原注在页边刊出,将1998年日本的涩谷正版所新发现的一部分信息在“中译者注”中刊出。但是在“异文”问题的处理上,正如日本学者大村等人指出的,广松版所依据的是阿多拉茨基版,但阿多拉茨基版并不是权威的、标准的版本,特别是广松没有参照《费尔巴哈》章的原始手稿,这使得广松版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尽管如此,广松版在学术史上仍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后来的研究(包括涩谷版在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广松版提出的“编”和“排”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立过程以及唯物史观最初明确的表述都具有启示作用,广松版提供的笔迹、删改等信息是中文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和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无法展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汉译广松版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汉译广松版出版以后,我国出现了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高潮,中国学者之间、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论此起彼伏,客观上实现了推进学术研究的效果,这里不再赘述。[14]
2008年,夏凡编译的《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二次编译梁赞诺夫版。这次编译将郭沫若故意遗漏的内容尽行恢复并译为中文,尤其是梁赞诺夫在《编者导言》中关于“原始手稿与文本的编辑工作”这一节的内容,使中国读者看到了完整的梁赞诺夫版。2010年9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又编译和出版了韩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郑文吉1990年以来主要文献学研究成果的文集,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一书。这本文集可以帮助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上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的争论,包括戈劳维娜的“季刊说”在内的典型观点[15],以及郑文吉本人的研究结论。总之,汉译广松涉版、汉译梁赞诺夫版以及郑文吉的文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深入的学术研究。
五、一点启示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特别是《费尔巴哈》章的手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反复修改、删除、补充、誊抄的,他们生前没能完成这部著作,更没有公开发表,因此并无权威的原始版本。同时,手稿没有连续和完整的页码顺序,由于保存不善还出现了手稿的残缺和佚失,因此,对于存在语言障碍的中国读者来说,如何编译和理解这部重要著作就成为一个晦涩难解并且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我国编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是,编译部门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的第一手资料的照片或影印件,我国也几乎没有文献考据和辨识方面的专家学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文献考据研究。于是,编译部门所参照的底版中的缺点和不足也保留在中文译本中,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纵观我国编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到一点启示:独立的文献学研究至为重要。
第一,重视“附属材料卷”(Apparat)的编译是深入研究的前提,这也是MEGA2不同于以往版本的独特之处,所谓“历史考证”的含义就体现在附属材料卷中。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1)校勘表(Korrekturenverzeichnis)介绍的是编者在研究和考订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时发现的笔误和印刷错误,及其更正的情况,它直接影响读者对于原文的理解。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时使用的是1844年奥托·维干德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当年的排版时漏掉了“我[并非]是空洞无物意义上的无,而是……”一句中的“并非”(nicht),导致意思完全相反,而中文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未做说明。这是否会引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误读施蒂纳呢?唯有独立、深入地去研究才能回答。(2)注释(Erlaeuterungen)是根据国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研究的成果编撰的,其中包括历史事实的考据、当时党派团体的简介、各种思潮的评述、基本术语和概念的诠释、各种历史典故、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证文献的出处和源流等等。这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意义非凡。但是,如果不先行从事有关研究,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学术积淀,不可能编写出高质量和有价值的“校勘表”和“注释”。MEGA2有关编辑整理(校勘表)、写作背景(注释)、修改过程(异文一览)的说明对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颇有裨益,但对非德语国家的读者来说极为不便且不易翻译,即便如此,我国学者也应以“辅助读本”的形式,有选择地编译其中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考证信息和结论。它一方面可以使更多的研究者进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语境,另一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又可以提高编译的质量,从而形成良性互动。
第二,关注国际学术界编译经典著作引发的新问题有利于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应该是供研究工作者进行研究所使用的版本,否则没有必要根据MEGA2重新编译,只需再版即可。这里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连问题为例。“编连”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和“排版”问题同等重要而且恰恰又是难于处理的问题。各版本的巨大差异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手稿笔迹的判读及排版可以尽量做到客观,而“编连”问题彰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准确表述唯物史观,它是对无形的思想的把握和理解,其难度可想而知,MEGA2迟迟不能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根本原因就是“编连”而非“排版”。2004年MEGA2先行版是按照写作时间排序,作为一个权威的、正式的、供研究的版本,MEGA2的编辑方针无可厚非。MEGA2并不追求逻辑的严整和形式的完善,而是尽可能地追求历史的客观和真实。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最为可靠的资料。但如果从“编连”的角度看,2004年MEGA2先行版按照写作时间排序的编辑方针不是争论的终点,恰恰相反,它是新研究的起点和工具,关键在于研究者如何开展个人独立的学术探索。因此,必须以MEGA2为基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有目的的取舍过程中再现他们思想发展和反复的过程,利用手稿中的加写、改写、未完成的段落、栏外增补以及注释等信息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手稿时的思想发展和变化并且为“编连”提供证据。实际上,这类文献训诂和考据意义上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在中国有相当长的历史渊源,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淀,因此,只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我国学者就能够开展独立的、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三,编译国外主要研究成果,公开编译部门的部分资料是形成严谨学风和产生扎实成果的重要保障。一项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和对待以往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实际上,国外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很多,包括《MEGA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故居文丛》等,我国多年来也有《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等,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或有关文献的试译稿,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背景资料、文献考证、国外学术动态等,马克思恩格斯提及或批判的人物与流派及其相关资料、国外重要期刊上的译文等等,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和文献资料。可是仍有许多重要的文献没有及时译为中文,许多中译文也只限于“内部参考”,从而限制了这些文献的功效。因此,目前除继续编译国外最新研究外,我认为应尽快公开这些“旧”资料,也可以专题的形式结集出版,从而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参阅这些资料。
总之,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译史可分为三个阶段:(1)郭沫若版阶段;(2)196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阶段;(3)2005年至2008年汉译版阶段。第三阶段的编译方针转向学术化,也是向第一阶段郭沫若版的回归。
从1938年郭沫若第一次翻译刊行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到2008重译梁赞诺夫版,似乎回到了起点,但这个起点已经是充满具体的丰富性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已经收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路、新方法。目前,在我国形成独立的文献学研究氛围至关重要。巴加图利亚在1965年曾经说过,“尽管从它的第一章发表至今已有40多年,从《形态》的完整出版至今已有30多年,我们还不能说这部著作的内容和意义已经被完全弄清楚了”。至今又一个4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能说“完全弄清楚了”[16]。为了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可靠的中文译本,针对原始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遮蔽的,而这种研究如果不是独立的就不能走得更远。
注释:
[1] 目前,国外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版本不多,主要是德文、俄文、日文和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其中的《费尔巴哈》章已经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梁赞诺夫版(1926年)、郎茨胡特/迈耶尔版(1932年)、MEGA1(1932年)、巴加图利亚新俄文版(1965年)、新德文版(1966年)、MEGA2试刊版(1972年)、日文广松涉版(1974年)、英文阿瑟版(1976年)、英文剑桥版(1994年)、日文涩谷正版(1998年)、小林昌人补译版(2002年)以及MEGA2先行版(2004年)等等。
[2] 郭沫若先生在该书《序》中指出,这个版本是他在20年前,即1927年完成的,他将译好的手稿交给神州国光社的王礼锡先生,但由于战乱,未能付梓。抗战期间,神州国光社将其印出,但郭沫若在“大后方”,一直未能见到这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的编者也曾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部分,在我国曾有郭沫若同志的译文,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741页)遗憾的是,笔者无缘,至今未能得见这一版。1942年7月,上海珠林书店出版了周建人(署名为“克士”)翻译的《费尔巴哈》章,书名为《德意志观念体系》。
[3] 为了研究和叙述方便,本文将采取“自然段标注法”,即根据我国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所划分的自然段顺序标号(“费尔巴哈”章共计151个自然段)。
[4][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编者导言、第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716页。
[7] 同上书,第33、41、66、69、82、85、87页。
[8] 同上书,第41、51、7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68、36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19、20、25、33、35、37、39、47、54、58、63、67、69、75页。
[11]《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12] 候才:《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文稿结构的重建》,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5期。
[13] [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编辑说明第11页。译者在这一版中修订了关于广松涉版“编辑方针”的译文。
[14] 参见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和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第一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日]大村泉等:《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版的根本问题》,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张一兵:《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夏凡:《〈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鲁克俭:《再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姜海波:《在文本与思想之间——从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连问题谈起》,载《理论视野》2010年第2期,等等。
[15] [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16] [前苏联]巴加图利亚:《〈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结构和内容》,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
(作者: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