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经受住考验的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钱学森。2021年是钱学森同志诞辰110周年。钱学森不仅是一位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顶尖科学家,还是一位心怀“国之大者”的战略科学家。在他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的人生旅程中,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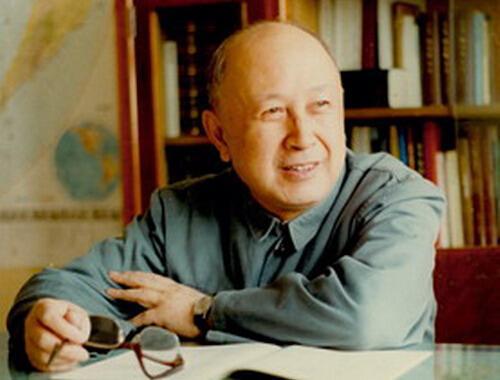
一、青年时代的思想启蒙
钱学森1923年至193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就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当时,执教附中的老师不少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在课堂上“宣传爱国、民主、进步的精神”。他曾回忆:“董鲁安是国文教员,但他在我们高中课里,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北上;他教导了我对旧社会的深切不满,对鲁迅先生的钦佩,也使我了解要祖国富强就非树立新政权不可。”董鲁安在钱学森的心里播下了一颗“思想革命”的种子,但此时他的思想还处在懵懂阶段,尚不懂得到底要树立什么性质的新政权。
1929年至1934年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求学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30年,他因伤寒向学校申请休学的一年时间里,在读“闲书”中对唯物史观产生浓厚兴趣;随后,他追本溯源,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利汉诺夫的《论艺术》、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等,“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
回校后,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和读书合作社,多次参加读书讨论会,从那里得知红军、苏区和红色政权的存在。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并前往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组织的读书会。留美期间,他与在国内的大学好友罗沛霖通信,约定找机会去革命圣城莫斯科。1947年暑期钱学森回国探亲时,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便对父亲钱均夫说,归国效劳,是其素志;但这种政府,断不能存在于人世间。直到1955年冲破美国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之后,钱学森才实现了“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的心愿。
二、壮年时代的理论学习
回国后,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在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科研和管理项目的实践经验,使他进一步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对科研工作的指导价值。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钱学森入党。至此,钱学森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实践到信仰,又以信仰为依托进行理论再学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钱学森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包括《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72年12月5日,他曾致函叶剑英说:“我是搞科学技术的,就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方面,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上层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组织。这个道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阐发得很清楚。”
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钱学森不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与体系,而且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坚信:“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
三、晚年时代的学术探索
20世纪80年代初期,钱学森退居二线后,以极大的热情,从科学技术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等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他向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身体力行地提出诸多思想与观点,包括建议总结近百多年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要“努力编出第二本《自然辩证法》”;主张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性智”与“量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进行基础研究的锐利武器;通过创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的科学最高概括”,“因而是指导人思维的明灯,是智慧的基础”。
“我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的。”这是晚年钱学森对一生信仰的坚定表达。
(来源:2021年12月8日第1528期《党史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