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投降迄今已80年,但中日历史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正视“战争记忆”:为中日历史认知寻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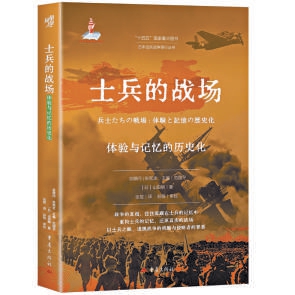
《士兵的战场:体验与记忆的历史化》 山田朗 著 张煜 译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揆诸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无论是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抑或“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均与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有关。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纷争,很大程度源于彼此对那场战争的认知不同,而这种不同的认知,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不同的“战争记忆”。
“战争记忆”的传承脉络与转化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成田龙一将战争样态的系谱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战争作为“情况”而被叙述的时期(1931—1945年)、作为“体验”而被叙述的时期(1945—1965年)、作为“证言”战争而被叙述的时期(1965—1990年)、作为“记忆”而被叙述的时期(1990年以后)。
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迄今已8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基本凋零殆尽,这就意味着拥有“战争记忆”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为极少数,作为“情况”而被叙述的战争几乎不再被提起;作为“体验”而被叙述的战争话题也逐渐沉寂;战争“证言”者正逐渐逝去;而战争作为“记忆”,不仅在中国学界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而且如下所述在中国民间可谓方兴未艾。
“战争记忆”最为重要的是传承问题。笔者认为,在“战争记忆”传承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不应忽视,那就是社会对“战争记忆”内容的理解。关于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李若愚(历史研究学者)“认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日本左翼对侵略的反省立场;第二类则是试图通过掩耳盗铃以湮没历史真相的右翼史观;第三类,或许也是持有人最多的一类,便是日本社会大部分老百姓的立场。他们对那段战争历史有着强烈的疏离感、陌生感”。
对于以上第二类的右翼分子,其之所以对那场战争抱持右翼史观,原因不外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使然,抑或“战争记忆”在转化为“历史”过程中的失真。对于前者,学界的批判性研究已是充栋盈车,不再赘述,在此主要谈谈后者。
《士兵的战场:体验与记忆的历史化》一书认为,“战争记忆”在被传承的过程中,经历了重构、选择,最终形成了“历史”。“战争记忆”的传承,与一般“记忆”的传承相同,大致可分为私人传承与公共传承。私人传承是个人或家族间传承的微观行为,而公共传承是以教科书记述为代表的宏观行为。通过个人或家族传承而来的具有私人性的“记忆”,通常包含许多个别且具体的特殊事例,而后在其所在地区或社会集体中被汇集,成为同代人的共同体验,这表现为“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可以说是战争年代体验者私人“记忆”群的最大公约数。以“集体记忆”为基础,建构、叙述而成的产物(教科书等),在学校等社会上流传,便形成记忆的公共传承。可以将其设想为以下流程:①私人传承→②集体记忆→③公共传承→④“历史”化。
中日“战争记忆”的重视落差
一些学者对李若愚所言的第二类人展开批判,让人误解为中日之间的各类历史问题主要来自于对“战争记忆”内容的理解不同,但其实第二类人在日本社会所占比重并不大,不足以影响中日关系,而真正形成影响的主要是第三类,即社会整体对“战争记忆”的重视程度。
具言之,当前中日两国对“战争记忆”的重视程度完全不同。中国每年都会举办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抗战胜利等纪念活动;初高中的历史课程以及大学的《近代史纲要》等课程一定会讲授相关内容。与此同时,民间的“战争记忆”被激活,典型的例子就是无处不在的抗日影视剧。与之相对,日本社会对“战争记忆”表现出疏离感、陌生感。即便有学者指出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具有选择性,即有选择性的记忆战争“受害者”身份,遗忘“加害者”身份,但其在社会中的关注度远不能望中国社会之项背。两国社会整体对那段“战争记忆”重视程度的不均衡性,才是导致中日两国之间历史问题悬而未决的根本性原因。
该书作者山田朗不无忧虑地指出:“日本社会整体的‘战争记忆’正不断淡化。”而山田在另一篇论文中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战争责任性的展开和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的诞生就是阻止这种“淡化”的趋势,也就是遏制日本社会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构和历史化需要传承的‘记忆’”。
为了撰写此书,作者一共查找了851部战争体验者的回忆录(单行本),以及逾1100份口述史料,显示了其宽广的视野、扎实的研究功底和实证性偏好。正如山田自己所言,这本书是以战争体验者自身记述的“体验”“证言”,以及体验者在翻阅公刊战史或对其进行批判性探讨后形成的,以“记忆”为素材,对理应得到传承的“记忆”群进行重构,对以太平洋战争为中心的战争进行历史叙述。因此,我们在阅读该书的时候,有时会有碎片化之感。
日本当探寻“隐匿的暴行记忆”
该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提及了未能留下有关战争的“体验”“证言”“记忆”的战死者:“无法诉说的战死者和能进行诉说的生还者之间,差别是无限大的,但实际也只有一线之隔。因为,决定战场上的生与死,只是‘运气’而已。在本书中出场的士兵,他们都是因为能够生还才留下了回忆和证言。”即便如上所述,作者找到了大量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但相较于战争中数百万的日军士兵,这些资料所描绘的“战争记忆”不过是一鳞片爪,我们据此来俯瞰战争的真实图景不免有群盲摸象之感,因此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要对此保持警惕。
该书略显不足之处在于所谓的“深层记忆”。作者认为“深层记忆”是私人传承容易断绝的那部分“记忆”,这里的关键词则是“隐匿”和“施暴”,其主要表现在战争暴行及违法行为的“记忆”。
该书也提到了日军使用毒气、自杀式攻击的“特攻队”,但对日军在包括中国战场在内的区域战争暴行的笔墨却不多。当然,作者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主要源于收集到的回忆录与口述资料中相关部分的占比甚少,“往往是战争亲历者有无法向家人(尤其是下一代)叙述的事情(残暴行为等),或者是迫于社会压力(包括有形或无形的)无法言明的场合”。对此,有学者认为日本社会要探究和传承这种“深层记忆”,必须克服狭隘的个人立场与民族主义情绪。
(作者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