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蘇維埃政權建立后不久,俄共(布)中央及各級黨組織就開始著手在東方國家開展革命工作。為領導對華革命工作,蘇俄及共產國際相繼成立了一些專門機構,這些機構及其代表對推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們彼此間缺乏相互配合,有時甚至互相干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華有關工作的推進。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蘇俄﹔共產國際﹔對華革命工作機構
蘇維埃政權建立后不久,俄共(布)中央及其下屬黨組織就開始著手在東方國家開展革命工作。為領導對華革命工作,並使工作更有組織性和針對性,蘇俄及共產國際相繼成立了一些專門機構,這些機構及其代表對推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往學者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關注了我們比較熟悉的幾個機構,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亞書記處、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等,但對於這一時期其他從事對華革命工作的機構,涉及較少。還有學者針對個別曾參與對華革命工作的機構進行了研究,但缺乏各組織之間的系統性研究。為了便於理解蘇俄在華開展的工作與各機構的關系,本文將結合中共創建時期蘇俄對華革命工作的進程,對曾參與中國革命工作的主要機構做一簡要梳理。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
一、對華工作准備時期的基本情況及相關機構(1917年11月至1920年初)
1917年11月到1920年初,是蘇俄對華革命工作的准備時期。由於蘇俄剛剛關注東亞和中國問題,同時也因為遠東地區與西伯利亞還處於隔絕狀態,對華工作主要是由遠東地區地方黨組織開展的,在俄國遠東和東亞的個別城市單獨進行,如伊爾庫茨克、哈爾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等,工作的固定聯系和接觸只是在哈爾濱與符拉迪沃斯托克,有時也在哈爾濱與布拉戈維申斯克之間進行。
這一時期,蘇俄對華工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十月革命勝利到1919年上半年,當時蘇俄尚無暇認真考慮對華關系,曾考慮把旅俄華工組織起來,與孫中山等進步力量建立聯系﹔第二個階段是1919年中到1920年初,此時蘇俄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開始考慮對華關系問題,初步制定了在華推進革命的措施。1919年9月,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以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身份赴西伯利亞開展工作,在此前后蘇俄又派霍多羅夫、楊明齋、布爾特曼、阿戈列夫、波塔波夫、柏良克、霍霍洛夫金等人來華開展工作,為下一階段維經斯基來華打下了基礎。隨著1920年2月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被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蘇俄對華工作拉開了大幕。
當時,蘇俄在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設置的曾參與過對華革命工作的機構有兩個,分別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和外交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使團東方局,這是最早涉及東方國家革命工作的機構。此外,在華的報社等機構也開始為蘇俄和共產國際服務。
(1)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1918—1924年)。1918年12月17日,為領導被白匪軍佔領領土上的黨的地下組織和游擊運動,俄共(布)中央決定成立由奈布特等5人組成的西伯利亞局,由於形勢發展,地點先后設於烏法、別列別伊、切列亞賓斯克、鄂木斯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現名新西伯利亞)等,是黨的直屬機關,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黨在西伯利亞的所有工作。1924年5月,隨著聯共(布)西伯利亞區委的成立,西伯利亞局撤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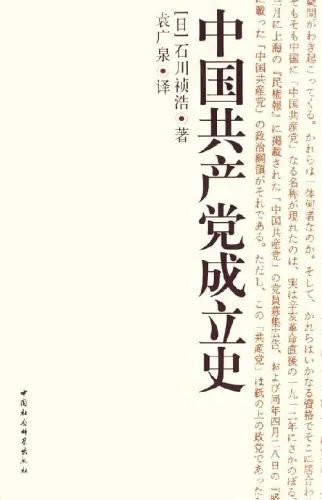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2)外交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使團東方局(1919年至1921年2月)。1919年在伊爾庫斯克成立,隸屬外交人民委員部,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是首任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1920年2月,楊鬆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外交事務全權代表。1919—1921年,加蓬先后任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外交事務副全權代表和全權代表,兼東方局主席。柳京也曾任東方局領導。其主要任務是處理蘇俄同遠東各國的關系同時參與幫助遠東各國開展革命的工作。

《中俄關系史料·一般交涉》(民國9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3年版。
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的職責是管理蘇俄西伯利亞地區的相關工作,西伯利亞使團東方局主要是開展國家間的關系,因此,從工作職能來看,它們都不是專門在東方國家指導和開展革命工作的機構。但實際上,它們在不同時期都或多或少地從事或參與了相關工作。比如,西伯利亞局寫過報告,建議成立東方局,以更好地促進東方革命運動的完成﹔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通過發展出版事業和建立組織聯系,開展有關革命工作。以上這些機構雖然是隸屬於俄共(布)中央,有些人也是中央派出的,但這一時期的具體工作基本上是由它們自行開展的,俄共(布)中央此時還無暇顧及也無法制定明確的工作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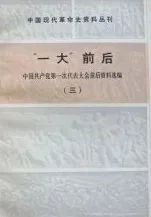
《“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3),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除了以上機構,這一時期還創辦了《上海俄文生活日報》、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駐上海辦事處等,它們后來成為蘇俄和共產國際來華人員的基地,並使其獲得公開活動的身份。
《上海俄文生活日報》由謝麥施科等傾向社會主義的俄僑於1919年9月在上海創辦,據其稱是當時“中國唯一之俄報”。1920年2月,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以5000美元買斷該報,並委派謝麥施科繼續擔任主編。自此,《上海俄文生活日報》得到蘇俄資助,成為一份受蘇俄控制的完全的布爾什維克報紙,該報社也成為布爾什維克在華的掩護機關和基地。東亞書記處成立后,《上海俄文生活日報》成為書記處所屬報刊。《上海俄文生活日報》還負責與東方民族部及中國各地的蘇俄人員進行通信聯系。《上海俄文生活日報》是中國第一個刊登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的報紙(1920年3月31日)。曾任上海俄文生活日報社工作人員的有考夫曼、古爾曼、諾維茨基、克拉辛等。《上海俄文生活日報》的印刷所是西比利亞印刷公司,其位於同一建筑內。《上海俄文生活日報》內還設有俄羅斯民主俱樂部,蘇俄骨干在此舉行集會,協商宣傳工作。由於報社更換過社址或有不止一個辦公地點,地址有幾個,分別是法租界霞飛路716號和英租界愛德華路、Seward Road12號(熙華德路,今塘沽路)、Seward Road拐角處的蓬路12號1層(Boone Road,今長治路)、Boone Road與Seward Road的交叉口等,后三個地址應該是一個。由於俄文報紙受語言所限,受眾較少,1922年9月,越飛決定創辦英文報紙(即1922年11月創刊的《新俄羅斯報》)取代它。不久,隨著蘇俄資助的停止,該報停刊。此后,根據需要又創辦了《新上海生活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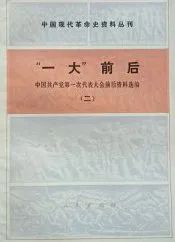
《“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駐上海辦事處於1919年在上海成立。總部設在莫斯科,在其他國家設有分部,上海辦事處位於現九江路與江西路交叉口。塔拉索夫、科索拉波夫等先后任辦事處的實際負責人,維經斯基應該也參與了有關工作。辦事處承擔了接收、轉撥經費,購買武器和物資,轉送從蘇俄寄來的電報、文件和宣傳品等工作,並積極進行宣傳。東方民族部及其領導人給維經斯基的電報等很多由辦事處中轉。辦事處與《上海俄文生活日報》被視作“並肩工作”的蘇俄在華的布爾什維克組織。由於檔案的缺乏,目前關於這一機構的很多情況還不十分清楚。
此外,在上海還有一些機構,如位於博物館路21號的西伯利亞購銷聯盟、位於九江路14號的俄國義勇艦隊上海分部、世界語學會(以位於四川路公益坊的新華學校為中心)、猶太人俱樂部(以位於四川路的基督教青年會為中心)等也或多或少從事著有關工作。
二、對華工作起步時期的相關機構及其基本情況(1920年春至1921年初)
1920年春至1921年初,是蘇俄對華革命工作的起步時期。隨著1920年春維經斯基來華,蘇俄對華工作正式啟動,蘇俄開始與中國各個派別相接觸,尋找革命聯合對象。這一時期,蘇俄對華具體工作仍然主要由地方黨組織開展。
1.起步時期的基本情況
這一時期成立或組建了5個參與中國革命工作的機構,分別是俄共(布)中央遠東局、共產國際執委會東亞書記處、羅斯塔-達爾塔電訊社中國分社、俄國共產華員局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此外,優林使團也參與了對華工作。
(1)俄共(布)中央遠東局(1920—1925),1920年3月3日成立於上烏丁斯克(現名烏蘭烏德),隸屬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1920年8月13日升格改組為與西伯利亞局同級的俄共(布)中央遠東局,10月隨遠東共和國遷至赤塔,下設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哈爾濱分局等分支機構,第一任領導有貢察洛夫、克拉斯諾曉科夫等,后來舒米亞茨基、楊鬆等也曾任領導,主要任務是管轄遠東共和國境內的黨組織,但也時常涉及東方國家有關事務。
(2)共產國際執委會東亞書記處(1920年5月至1920年7月)。1920年5月在上海設立,是一個臨時集體領導中心,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是臨時局主席,但維經斯基是實際創建者,並在具體工作中發揮了主要作用。書記處由中國支部、朝鮮支部、日本支部(處於萌芽狀態)組成,中國支部計劃在學生和沿海地區工人組織中成立黨的基層組織,進行建黨工作﹔在軍隊中進行共產主義宣傳﹔對工會建設施加影響﹔組織出版工作。在東亞書記處存在的短短幾個月時間裡,中國支部在出版、宣傳、組織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績,特別是學生工作成效明顯。東方民族部成立后,東亞書記處改組為東方民族部上海分部。
由於檔案的缺乏,東亞書記處的有關情況還需要進一步証實。目前,我們隻在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的有關信件和報告中看到有關它的情況。而它的成立是否經過共產國際批准,它是否為共產國際的下屬機構,實際上並沒有檔案能夠証明。1920年7—8月,列寧建議委派馬林到中國作為共產國際駐遠東的代表,其任務之一是“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因此,當時列寧、俄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很可能並不知道東亞書記處的成立,它只是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要求維經斯基在上海工作期間臨時成立的。1920年9月,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才向共產國際報告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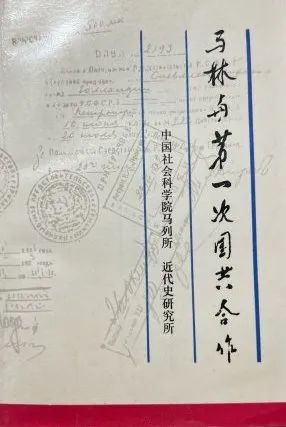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3)羅斯塔-達爾塔電訊社中國分社。羅斯塔(Pocтa)是蘇俄於1918年成立的俄羅斯電訊社,1925年改名塔斯社(TACC)﹔達爾塔(Дальта)是遠東共和國於1920年設立的遠東電訊社,1922年11月隨著遠東共和國的撤銷,達爾塔社不復存在。1922年以前這兩個通訊社在中國有時單獨活動,有時合二為一,但實際都是以通訊社名義,兼對華宣傳和搜集情報兩項工作,受蘇俄和共產國際雙重領導。中國分社成立於1920年5月,總部設在北京,首任社長(或經理)為霍多洛夫。后來,馬蘭諾夫斯基也負責過通訊社。此外,還有上海華俄通訊社、哈爾濱的北滿通訊社、廣州華俄通訊社、奉天華俄通訊社。在中文報紙上羅斯塔-達爾塔通訊社中國分社被稱為華俄通訊社或中俄通訊社。
(4)俄國共產華員局(1920年7月至1922年),1920年7月成立於莫斯科,9月遷至伊爾庫斯克,11月遷至上烏丁斯克,是旅俄華人共產黨組織的中央領導機構,隸屬俄共(布),受俄共(布)領導,是其國際支部之一,主席為安龍鶴。該機構負有對俄、華的雙重使命:既要發動廣大華工積極參加蘇俄的政治生活,又肩負著在中國進行社會革命的責任——組織中國無產階級及在華建黨。共產華員局與蘇俄和共產國際有關機構的合作並不融洽,也未能開展有效的活動。隨著俄共(布)對華工作機構的逐漸健全以及蘇俄與中國共產黨直接聯系的建立,1922年,俄共(布)解散了共產華員局及其地方組織。
(5)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1920年7月至1921年1月)。由於遠東工作的擴大,需要成立一個統一的機構,集中領導東方國家共產黨的工作。1920年6月26日,西伯利亞局決定在伊爾庫斯克建立東方民族部,經費由局方提供。7月27日,東方民族部首次召開會議,決定由貢察洛夫同志擔任東方工作全權代表,布爾特曼為主席,加蓬為副主席。9月末,遠東局書記、俄共(布)中央外貝加爾省委主席勃隆施泰恩進入主席團,任主席團書記兼情報科科長。由於貢察洛夫是西伯利亞副總司令部政委,常駐鄂木斯克,而加蓬是外交人民委員部副全權代表,忙於西伯利亞使團的日常工作,因此,主席團日常工作由布爾特曼和勃隆施泰恩主持。東方民族部的主要任務有二:一是在所在國(即本土)給予中國、朝鮮、日本和蒙古的革命組織幫助﹔二是幫助旅俄(特別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東方民族代表(即旅俄僑民)的革命工作。
東方民族部下設中國科、朝鮮科、蒙藏科、日本科(未能建立)、報道科等科,由於中國、朝鮮、日本尚未建黨並缺少有權威的領導人,各科領導均由俄共(布)黨員出任。中國科科長是阿勃拉姆鬆,書記是霍霍洛夫金,其大部分機關和工作人員都在中國工作。根據工作需要,東方民族部設符拉迪沃斯托克分部、上海分部等分支機構,俄國遠東以符拉迪沃斯托克為中心,領導布拉戈維申斯克、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科爾斯克-烏蘇裡斯克(雙城子)等地的工作,均秘密行動﹔上海分部是東方民族部在中國的遠東工作中心,由東亞書記處改組而來,領導包括哈爾濱在內所有的在華機關。
(6)優林使團(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1920年6月,遠東共和國在蘇俄授意下派出了以優林為團長的赴華談判外交使團。8月底,優林幾經輾轉,以商務總代表身份抵達北京。優林使團來華的目的主要是解決通商條約、在華俄僑、停止俄使待遇、庚子賠款、在俄華僑、領事裁判權與中東鐵路等問題。優林使團雖然是為了解決國家間的問題,但實際上也秘密執行了在華開展革命和聯絡等工作。如1920年7月4日,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就是以優林代表團秘書的身份,以“視察工商實業狀況”為名來到北京召開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優林使團還承擔了向蘇俄在華代表轉交活動經費等工作。
此外,在中國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還組成俄國共產黨員代表會議,並於1920年7月初舉行了第一次俄國共產黨員代表會議,討論了在中國的有關工作。
這一時期的蘇俄對華工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20年春到1920年中,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發揮了主要作用。以維經斯基被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到中國為標志,蘇俄對華工作正式啟動。不久,斯托揚諾維奇(化名米諾爾或米涅爾)被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從哈爾濱派到天津。在此前后,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的馬馬耶夫和阿勃拉姆鬆來到哈爾濱。這一階段,蘇俄對華革命工作進展順利,其代表與中國所有派別的領袖都建立了聯系,並幫助創建了中共早期組織。
第二個階段是1920年7月到1921年初,蘇俄對華革命工作得到更多機構的關注。1920年7月成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是主要負責部門。同時,7—8月,列寧建議派馬林來華作為共產國際駐遠東的代表。同年夏,遠東共和國派出優林使團來到北京。9月,外交人民委員部派朴鎮淳赴中國。
這一時期,在華工作的人漸漸多起來,除了之前來華的同志繼續工作,蘇俄又不斷派遣使者。1920年9月,斯托揚諾維奇等來到廣東,以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訊社記者身份開展工作。同年秋,馬馬耶夫來到武漢考察工作。10月,東方民族部派霍霍洛夫金為特使,赴中國負責交換情報、對在華分支機構(包括維經斯基)給予指導、建立在華分支機構與東方民族部的固定聯系及組織機構、召集負責人員的代表大會並籌備中國全境的革命代表大會、運送和變賣珠寶等。此時,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成員霍齊全姆斯基也在天津工作。同年11月底,東方民族部又決定派耿金和羅姆赴中國考察。但以上三人可能未能成行。同年11月至1921年4月,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經布拉戈維申斯克來華工作。據說,維經斯基回國前,赤塔的國際工會聯合會遠東局還派出了弗羅姆別爾格。截至1920年底,有十幾位蘇俄共產黨員在中國工作。
這一時期蘇俄在遠東地區有幾個活動中心,從蘇俄國內的領導中心來看,1920年7月前主要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民族部成立以后,領導中心轉移到伊爾庫斯克﹔從中國國內的活動中心來看,1920年春以前哈爾濱和京津地區是蘇俄在華比較活躍的中心,1920年5月以后上海逐漸成為蘇俄在中國最主要的基地。
2.起步時期各工作機構之間的矛盾
從以上介紹可以看出,蘇俄對華工作最初是由地方黨組織自主開展的,由於蘇俄剛剛在東亞開展革命工作,面臨的國內外形勢非常復雜,中央與地方及駐華機構雖有通信及人員往來,但中央與地方黨組織缺乏充分的溝通,中央對中國革命情況和有關工作進展的了解並不全面、及時,對整個工作缺乏直接指導和有效規劃,這就導致各個系統和組織之間關系復雜,工作任務不清,工作人員常常在不同機構兼職,各機構和駐外代表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和配合,組織上比較混亂。
在以上機構中,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遠東局的職責分別是管理蘇俄和遠東共和國自身黨的相關工作,西伯利亞使團東方局和優林使團主要負責開展國家間的關系,共產華員局擔負在華建黨的使命,東亞書記處和東方民族部的職責就是在東方國家開展革命運動。但當時的問題是,各個機構都插手東亞革命問題,互相掣肘,特別是對華工作方面,它們分別與中共、無政府主義者、大同黨、孫中山、陳炯明、吳佩孚等聯絡,在一段時間裡局面相當錯綜復雜。
東亞書記處是第一個成立的專門開展東方國家革命工作的機構,其領導早就發現了組織混亂的問題。1920年9月1日,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把現為遠東工作的各機關集中由一個直屬共產國際或俄共(布)中央的中心機構來協調,這一機構就是東亞書記處,解除西伯利亞局和遠東局所有掌握東方語言或英語並從事東方工作的人員的工作,把他們交由東亞書記處調遣。
優林抵達北京后,在華俄國人也意識到缺乏配合、互相干擾的問題,並試圖予以解決。1920年9月初,5名俄國共產黨員從上海趕到北京,試圖解決組織統一問題。維經斯基在天津同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成員霍齊姆斯基私人會見時得知其要與優林聯系進行工作,並接受優林的領導。此后至9月10日,在中國各地工作的蘇俄代表在北京召開會議,經過討論,他們決定以優林為領導,並初步確定了分工負責人,負責日本方面工作的是波波夫,負責與上海方面中國人聯絡的可能是維經斯基。根據這一安排,維經斯基把所有情報資料都寄給了優林,還要求東方民族部的勃隆施泰恩和阿勃拉姆鬆等人服從優林的領導,並根據優林的安排,一度未與東方民族部再進行直接聯系。
優林的做法加劇了與東方民族部的矛盾。東方民族部成立后維經斯基本應接受其領導,但優林使團來華后,東方民族部與上海分部的聯系就被優林接管過去了,維經斯基未再向其報告過工作。對此,東方民族部相當不滿。9月30日,東方民族部致電維經斯基,要求其作為東方民族部全權代表領導在華工作人員,經常報告活動情況,並進行工作請示。10月下旬,勃隆施泰恩和阿勃拉姆鬆致信維經斯基,指出霍齊姆斯基的聲明是因誤會和不了解才做出的,西伯利亞局已經向他做了相應說明﹔同時,東方民族部是唯一擁有全權在東方國家進行革命工作的組織,因此阿勃拉姆鬆等人應直接向維經斯基請示工作,維經斯基同優林的關系應僅表現在他對工作有用時才與之接觸,必須消除由優林引起的完全偶然的障礙。
除了與優林使團的矛盾,東方民族部成立后還與多個機構粗齲不斷。
第一,與外交人民委員部。1920年12月,東方民族部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指出,外交人民委員部一方面要求東方民族部提供幫助,另一方面卻不同東方民族部協調,就直接開展支援共產黨的工作。如外交人民委員部繞過東方民族部向朝鮮社會黨人朴鎮淳調撥400萬盧布,其實,朝鮮有真正的共產黨組織,急需經費的是他們。外交人民委員部還給一個蒙古代表大量白銀和珠寶,而東方民族部下屬的蒙藏科卻無法控制尚未正式建立的蒙古人民革命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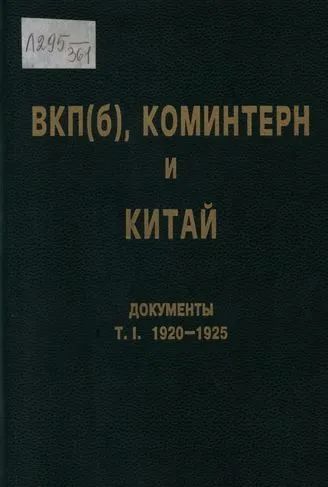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0-1925. Документы. Т. I.М., 1994.
第二,與共產華員局。東方民族部對共產華員局及其組成人員的評價一直不高,1920年10月27日,東方民族部致電共產國際代表,要求全部東方工作暫時由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負責,還希望俄共(布)中央解釋共產華員局具有哪些職責。11月13日,東方民族部報告俄共(布)中央,請求在中共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共產華員局歸東方民族部管轄。
第三,與遠東局。1920年11月,加蓬致電外交人民委員部、加拉罕、俄共(布)中央、共產國際執委會科別茨基等指出,截至目前本部最大的障礙是與遠東局的關系尚不明確。他認為遠東局機構不健全,無相應工作人員,不能全面開展工作,卻奢望承擔此項工作,於是造成雙方的分歧,導致東方民族部給各支部和國外情報人員發送的情報資料被攔截。加蓬認為,遠東局隻能管轄俄國遠東地區的黨組織,而中國、朝鮮和蒙古的組織領導工作應集中在東方民族部這個中心,中央需要對此發出強硬的明確指示。具體地說,雙方的矛盾集中在朝鮮問題上。朝鮮組織分為伊爾庫茨克派和上海派,如與維經斯基一同來華的金萬謙屬於伊爾庫茨克派,朴鎮淳則是上海派。朝鮮兩派在爭奪運動領導權的過程中,分別得到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后來是遠東書記處)和遠東局的支持,正如馬林指出的:“兩派朝鮮人之間的爭吵,本來是伊爾庫茨克與赤塔之間的糾紛,特別是舒米亞茨基同志與克拉斯諾曉科夫同志之間的糾紛。”
第四,與西伯利亞局。西伯利亞局雖然是東方民族部的上級機關,但雙方關系並不融洽,西伯利亞局曾向俄共(布)中央建議把東方民族部遷往赤塔,認為遠東共和國政府所在地赤塔才是東方國家所有情報匯集的中心。對於俄共(布)中央根據這一建議做出的決定,東方民族部認為,這會導致其組織和工作的毀滅,並堅持留在伊爾庫斯克。此外,東方民族部還認為,西伯利亞局隻不過是一個向中央請示的中轉站,對於領導和加強遠東各國共產黨的工作,該局隻把它當成次要任務,而且它也起不了領導作用。因此,1920年11月23日,加蓬致電外交人民委員部、加拉罕、俄共(布)中央、共產國際執委會科別茨基等提出,東方民族部應該同共產國際建立穩固的直接聯系,取消西伯利亞局的領導,派一名中央級黨的負責干部加以領導。
組織上的混亂,導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東方民族部缺少經費和干部。1920年12月,東方民族部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指出,至今未從中央機關得到1美元或其他貨幣,雖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一些珠寶,並答應再給10萬美元,但鑽石變賣需要一段時間,答應給的錢至今還沒收到,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開展工作。1920年9月15日,布爾特曼致電伊爾庫茨克省黨委主席柳金,說明該部干部奇缺,請求任何知曉漢語等外語的共產黨員干部的派遣,均需經東方民族部許可﹔不征用中國等國任何共產黨員負責干部。
其次,在推進東方國家工作方面進展緩慢。東方民族部當時是專職從事對東方國家革命工作的機構,但其存在期間隻收到過維經斯基一次正式工作報告,即1920年8月17日的信。盡管東方民族部及其領導幾次要求維經斯基報告活動情況,但仍未收到有關工作報告。東方民族部雖然希望派信使赴華,但出於各種原因,大多未能成行。因此,東方民族部對中國等東亞國家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也沒辦法進行具體工作指導。就當時蘇俄在華最主要的代表維經斯基來說,他先后接受過遠東局、東亞書記處、東方民族部、優林使團等多個機構的領導,這種混亂的局面也對他的工作產生了不利影響。1920年下半年,蘇俄對東方國家的工作成效不大,中國共產主義者代表大會未能召開,與日本的聯系未能建立,朝鮮黨各派別分歧加劇。
要解決這種無序的局面,迫切需要整合現有機構,成立一個統一的工作部門。
三、對華工作展開時期相關工作部門的統一(1921年初以后)
1921年初開始,蘇俄、共產國際對華革命工作進一步展開。由於之前從事對華革命工作的部門比較混亂,於是經蘇俄和共產國際批准,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工作部門——共產國際遠東執委會書記處。在蘇俄的指導下,遠東書記處及駐華代表的努力下,蘇俄基本確定了中共作為其工作對象。
1920年下半年,鑒於遠東工作的混亂,東方民族部建議將其改組為直屬共產國際的部門。1920年9月15日,東方民族部收到西伯利亞局來電,決定將其改組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10月27日,東方民族部召開會議,建議黨中央組成遠東書記處,提出初步的編制、人員,並決定致電共產國際,說明組建書記處的必要性。此后,東方民族部又多次開會討論此事,並決定派專人赴莫斯科匯報情況,提出擬成立的直屬共產國際的遠東書記處的編制構成。根據1921年1月5日俄共(布)中央的決定和1921年1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定,1921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在東方民族部的基礎上正式成立。2月12日,共產國際駐遠東全權代表發布第一號命令,宣布包括東方民族部、外交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使團等在內的所有機關的工作都轉交給遠東書記處。2月16日,共產國際駐遠東全權代表發布第二號命令,宣布了外交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使團和東方民族部取消后相關人員在遠東書記處的任職通知。
(1)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1921年1月至1922年2月)。1921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在伊爾庫斯克正式成立,隸屬共產國際執委會,舒米亞茨基為共產國際駐遠東全權代表,加蓬為副全權代表,書記有弗拉索夫斯基、鮑德裡茨基、尤金等。下設中國、朝鮮、蒙藏等支部,中國支部俄方書記是阿勃拉姆鬆,俄方副書記是符拉索夫斯基,成員有霍霍洛夫金。1921年3月起,張太雷任中國支部中方書記。截至1921年11月中旬,遠東書記處共有113名工作人員。遠東書記處的任務是:其一,向共產國際報告遠東各國工人運動及革命運動的情況,向各國革命組織傳達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和任務﹔其二,幫助各國建立組織並開展革命斗爭。
隨著遠東書記處的成立,蘇俄對華工作部門得到統一。原來蘇俄共產黨各級組織、共產國際、外交人民委員部等系統分而治之的情況開始好轉,蘇俄在遠東的工作基本統一到共產國際系統,在對華工作等方面也取得進展。盡管由於維經斯基回國,中國國內的工作一度停滯,但同年春中共代表赴俄與遠東書記處建立直接聯系,這又為后來的工作打下重要基礎。在遠東書記處的支持下,中共作為中國唯一共產黨的地位在共產國際三大上得到蘇俄的承認。與此同時,1921年6月,遠東書記處派尼克爾斯基來上海工作,並任命馬林為書記處成員。同年10月初,利金作為駐華全權代表被派往中國。馬林來華則推動了中共一大的召開,中共正式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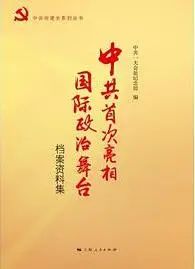
《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台(檔案資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遠東書記處雖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有些部門的分歧並未因遠東書記處的成立而彌合。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局仍然矛盾重重,優林甚至評價它“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把精力都浪費在與遠東局的權力之爭上。特別是在朝鮮黨的問題上,遠東書記處明顯支持伊爾庫茨克派。1921年2月23日,舒米亞茨基致電俄共(布)中央,提出遠東局和遠東共和國干涉遠東書記處的工作,損害了朝鮮工作。2月26日,舒米亞茨基再次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其命令遠東局不要干涉有關朝鮮黨的工作。由於蘇俄地方黨組織和遠東書記處分別支持不同的派別,兩派矛盾激化,甚至出現了流血事件。為解決這一問題,1921年11月,共產國際主席團組成三人委員會,調查並做出對朝鮮問題的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俄共(布)中央都予以批准。這一報告引起了舒米亞茨基的抗議,還導致了共產國際內部的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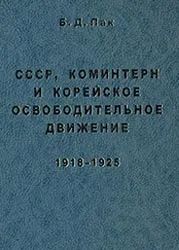
ПАК Б.Д. СССР ,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орейско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1918-1925, Москва :ИВ РАН , 2006.
第二,遠東書記處的聯絡、溝通等工作存在問題。一是遠東書記處與中央(即共產國際執委會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聯系不夠,這也進一步妨礙了上海同蘇俄的溝通和聯系。二是遠東書記處與中國等東方國家的聯系不暢。馬林在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指出,在伊爾庫斯克設立一個共產國際的辦事處對遠東工作毫無用處,因為伊爾庫斯克地處偏遠,很難經中國東北與東方國家保持經常聯系,即便是赤塔,同樣也不方便,馬林從未收到過從伊爾庫斯克來的文件。馬林雖然是遠東書記處的成員,但從未參與過其任何決策和全面工作,與其並無組織上的聯系。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遠東書記處沒能在東方國家建立有效的執行機構,使書記處工作效果有限。三是其聯絡站與駐外機構的關系有問題。遠東書記處規定,其聯絡站要獨立於蘇俄合法駐外機構之外,秘密進行活動。但在實踐中,其聯絡站卻不得不利用蘇俄的一些駐外機構。四是聯絡站的設置存在浪費問題,即對現有聯絡站的利用不夠,其工作性質僅限於信件交往和書籍、人員中轉的技術性機構,事實上完全可以在情報資料搜集、當地情況研究等方面再擔負一些任務。此外,在天津和北京的一些聯絡站是多余的。
第三,遠東書記處的經費使用有問題。一是書記處對於撥款的批准條件不符合工作實際。書記處對於國外工作的撥款要求有預算,並要求每項預算隻有在具備明確內容,即工作本身有嚴格明確方案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但由於秘密工作條件本身的限制,常常不可能有完整的工作方案。二是書記處給東方各個黨的預算撥款不穩定,經常變動不定,對各黨開展工作產生不良影響。
基於以上原因,1922年2月,在遠東書記處協助開完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后,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撤銷遠東書記處,舒米亞茨基也被安排到赤塔工作。隨著遠東書記處的撤銷,東方工作的領導中心暫時被轉移到莫斯科,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下屬的遠東部負責整個遠東地區的工作。
(2)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1921年中至1923年1月)。1921年中,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成立,主任是特立力塞爾。1922年,維經斯基接任主任,成員還有斯列帕克和考夫曼。遠東部隻存在了很短的時間,由於人手不夠,遠離東方,很難開展有效的工作。1923年1月,遠東部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遠東局替代。
四、小 結
中共創建時期,蘇俄和共產國際曾有多個部門和機構開展對華革命工作,它們通過不同渠道向中國派出代表。通過對以上機構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些認識。
第一,這些機構分屬不同的系統。一是蘇俄共產黨系統,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及其下屬的東方民族部、俄共(布)中央遠東局和共產華員局﹔二是共產國際系統,如共產國際執委會東亞書記處、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等﹔三是外交人民委員部系統,如外交人民委員部及其下屬的西伯利亞使團東方局。此外,蘇俄一些在華辦事機構,如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駐上海辦事處、羅斯塔-達爾塔電訊社中國分社、《上海俄文生活日報》,以及遠東共和國的優林使團等也參與了對華工作。
第二,蘇俄和共產國際及其有關機構對推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向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及蘇俄的情況。一方面通過中(華)俄通訊社在中國報刊上發稿,發表了大量關於蘇俄的消息﹔另一方面加強宣傳工作,提供書刊,幫助開辦又新印刷所,翻譯和印刷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寄來的材料和《論俄國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等圖書。以上工作讓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加直觀地了解和認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進一步堅定了走這一道路的決心。
二是提供開展活動的經費。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向中共提供了大量經費,1921年12月施存統在日本被捕后說,“最初與上海的俄國過激派代表有關系,每月接受宣傳費約千元,干部們每月報酬三十元”。據鄭佩剛回憶,維經斯基曾通過陳獨秀交給他二千元,作為又新印刷所的開辦費。劉石心也曾回憶,《勞動者》刊物創辦后,“俄國人米諾幫助我們印刷費”,“通過梁冰弦給些錢”,“后來陳獨秀來組織廣東共產黨時”,“我們沒有加入共產黨”,“此后,俄國人就不再找我們”,“《勞動者》因缺乏經費也隻好停刊”。另據俄國檔案,1920年3月韓人社會黨代表李翰榮在伊爾庫斯克得到共產國際資助的400萬盧布,但還未出發就被加蓬截了200萬,到北京又被優林留了100萬,在上海他給“陳獨秀2萬日元,用於開展共產黨的工作”。根據日本檔案,蘇俄代表多次給陳獨秀宣傳費等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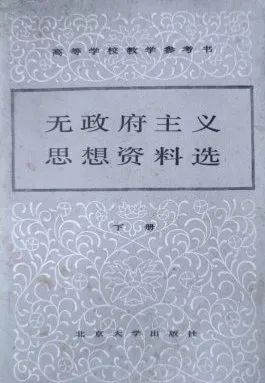
《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三是幫助創建有關共產黨組織。維經斯基來華的目的之一就是在華建黨,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在北京召開的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討論了“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組織中國共產黨”等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社會主義者同盟,到社會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再到一些地方共產黨早期組織和中共的創立,都有維經斯基等蘇俄代表的參與。
第三,有關機構的工作也存在一些問題。由於機構眾多,主管領導也不同,多個機構都從事對華工作並派出代表,一度造成混亂的局面。俄共(布)遠東局向中國派出維經斯基,他與包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等在內的各個派別聯絡過。外交人民委員部派出的朴鎮淳,得到遠東共和國的支持,在中國主要與大同黨聯絡,也曾與陳獨秀等人接觸。受蘇俄政府派遣以遠東共和國名義來華的優林使團,既從事外交工作,也開展革命工作。東方民族部成立后,維經斯基本應轉受其領導,卻被優林接管過去,以致1920年8月中旬后,東方民族部未收到維經斯基的任何工作報告。東方民族部的繼任——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成立后,中共不僅幾個月沒有收到任何指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們彼此間缺乏相互配合,有時甚至互相干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有關對華工作的推進。組織混亂問題直至大革命時期也未能解決,成為很長時間裡中國革命面對的一個障礙。
來源:《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第14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版
